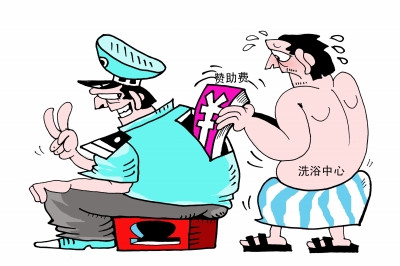國人矚目的“薄熙來案”庭審已經結束,該案審判程序前所未有的公開、透明,給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讓國人看到了法治的進步。整個庭審過程,在審判長耐心、平和的主持下,控、辯雙方圍繞爭議的焦點事實,展開了積極、激烈的攻防對抗。其中,控、辯雙方圍繞爭議的証據問題,靈活運用各種証據規則進行質証,既是本次庭審的一大特點,也堪稱我國1996年刑訴法修改確立“控辯式”審判模式以來庭審的經典之作,實有必要從証據法理和司法技術的層面加以點評、總結。
証人作証資格問題
在本案審理中,辯方曾多次質疑控方証人的作証資格問題,這是典型的以否定証人資格進而否定証詞的辯護策略。例如,在關於受賄罪名的辯護中,公訴人指控被告人3次收受唐肖林賄賂共計折合人民幣110.9446萬元,並當庭播放了証人唐肖林的証詞。對此,辯護人答辯稱“唐肖林收了250萬元,本身就已犯罪,在此情況下他還作証,是不合適的”。這顯然是對唐肖林証人資格的質疑。
筆者認為,辯方的質疑不成立,這是因為,証人唐肖林雖然在他案中因收受他人財物而構成犯罪(已另案處理),但他在本案中作為行賄人指証受賄人,並不存在角色沖突問題,屬於証據法理上的“污點証人”,仍然具有証人資格。
再如,在關於被告人貪污罪名的辯護中,辯護人對証人薄谷開來的作証能力提出質疑。認為薄谷開來在之前的故意殺人案審判中已經查明其有精神障礙,“這樣一個精神狀態的人能否作証,作証時是否清醒不得而知,這些証據能否可信,都值得懷疑”。這顯然又涉及証人作証資格問題。
對此,我國刑訴法第6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証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証人。”換言之,隻有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才會喪失証人資格。而從本案情況來看,根據公訴方的回應,証人薄谷開來為本案作証的時間是在其服刑期,根據對其所作精神鑒定,結論是薄谷開來的控制能力減弱,但不能証明其思維和証明能力減弱,且其在作証時已經消除了導致其控制能力減弱的條件(服刑期無法服用精神藥物)。因此,証人薄谷開來在作証時完全具備刑訴法規定的作証資格,辯方的觀點不能成立。
所謂“外圍証據”問題
在本案庭審中,被告人曾多次在証據答辯中提出所謂“外圍証據”的觀點。例如,針對起訴書指控的收受唐肖林財物的問題,被告人答辯稱:“剛才公訴人提出的証詞証言都是外圍証言,絕大部分都是外圍証據,與本案關系不大,不能証明我有罪。”但實際上,我國証據立法、理論和實務中並無“外圍証據”這一術語。筆者認為,被告人所謂的“外圍証據”,其實指的是“間接証據”,即不能直接証明犯罪行為系被告人實施的証據。被告人以“外圍証據”(間接証據)作答,意在反駁控方指控因缺乏直接証據而証明力不足。
但在証據法理上,被告人的這一反駁是難以成立的,因為,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証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3條明確規定:“沒有直接証據証明犯罪行為系被告人實施,但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一)據以定案的間接証據已經查証屬實;(二)據以定案的間接証據之間相互印証,不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無法解釋的疑問;(三)據以定案的間接証據已經形成完整的証明體系;(四)依據間接証據認定的案件事實,結論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懷疑;(五)運用間接証據進行的推理符合邏輯和經驗判斷。”這意味著,即使案件中沒有直接証據而僅有間接証據,隻要間接証據能夠形成証據鎖鏈,且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法定証明標准,仍然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因此,所謂“外圍証據”(間接証據),仍然是証據,而且是定案根據。
非法証據排除問題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由於被告人當庭翻供,公訴方被迫頻頻引証被告人在紀檢調查期間所作認罪自書。作為一種辯護策略,被告方轉而強調其在紀檢部門調查期間所作的認罪自書材料系非法証據,但法庭並未因此啟動非法証據調查程序,那麼,法庭的這一做法是否合法?
筆者認為,根據我國刑訴法第56條明確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証據情形的,應當對証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証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証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換言之,法庭不能僅僅依據被告方的申請即隨意啟動非法証據調查程序,而是要求被告方首先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即被告方首先應當盡到“爭點形成責任”。所謂被告方的“爭點形成責任”,是指在非法証據排除案件中,被告方雖然不承擔証明証據取得合法性的舉証責任,但卻有責任提供可供調查非法取証行為的相關線索或者材料,如非法取証的時間、地點、行為人等情況,使法官對該証據取得的合法性產生合理懷疑。若被告方僅僅提出排除非法証據的申請,但卻沒有或者未能盡到“爭點形成責任”,則法庭將無法對証據取得的合法性產生合理懷疑,進而也就無法啟動非法証據調查程序,展開法庭調查。在本案中,雖然被告人一再宣稱其所作自書系在不正當壓力和誘導下寫成,卻未提供非法取証的具體線索或材料,如時間、地點、非法取証行為人等情況。相反,被告人曾當庭承認在紀檢調查期間曾受禮遇優待。
綜上,所謂非法証據的問題,純屬辯方的一種抗辯策略,意在否定先前自書的真實性,為其翻供提供合理支撐。對此,法庭自不必再展開專門的法庭調查。
品格証據運用問題
在英美國家的刑事訴訟中,“在交叉盤問時攻擊証人的誠信度時,品格証據就是一個決定性因素。”本案中,被告方也頻繁運用了這一戰術,試圖通過抨擊控方証人的品格來否定其証言的真實性。例如,在關於受賄罪的辯護時,被告人對証人唐肖林的証言極力否認,把唐肖林說成是騙子,說成是為檢舉被告人而達到立功目的;再如,對於証人王立軍的証言,被告人認為:“此人品質極其惡劣,一是當場造謠,二是把水攪混,這種人作為重要証人進行舉証,有失法律公信力。”
雖然,我國司法實務中並不完全排斥品格証據的運用,例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品格証據就是非常重要的定案証據。然而,在本案中,被告方對品格証據的“戰術”運用並不成功,主要原因在於本案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控方証人品格的攻擊,僅僅是一面之詞,缺乏証據的支撐,辯方實際上僅僅是對証人的品格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而未舉出任何証據予以証明。在証據法理上,若要質疑証人的品格(如誠信度),必須提供相應証據予以証明。例如,可以要求法庭通知証人的鄰居出庭就証人的聲譽作証。若僅僅只是針對証人的品格發表自己的意見,而未能舉出任何証據予以証明,則很難動搖証人証言的真實性。
(作者為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