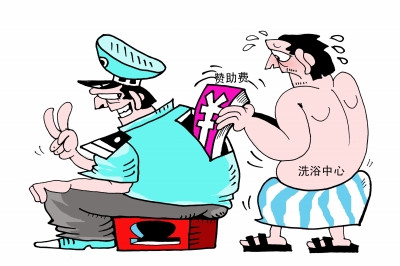關於教育券,多年前曾流行的一些陳詞老調最近又浮出水面。猶記得2003年年底,湖北省監利縣開始實施弗裡德曼式教育券的“義務教育卡”改革,在全國引起不小的轟動,筆者當時任監利縣教育局局長,親歷了這場僅持續了一年時間的改革實驗。
監利縣當時是把政府對教育僅有的投入——教師工資總額的一部分(30%)拿出來,根據學生人數分攤給學校。方案實施后出現如下現象:
一是農村小學之間,公辦教師工資經費向代課教師流動。因為前者的工資基數高,后者的基數低。二是正常配編學校的經費向缺編的學校流動,即師生比越高的學校教師工資就越高。三是長教齡和高職稱的教師工資經費向短教齡、低職稱的教師流動。四是村辦小學教師工資經費向聯村辦中心校流動,因為很多村辦小學學生少,聯村辦學因地理條件好、人口相對集中。
上述現象引發的問題是:嚴重挫傷了村小教師的積極性﹔嚴重挫傷了高職稱教師和長教齡教師工作的積極性﹔造成了學校之間的惡性競爭。為了提高教師待遇,學校隻好爭奪生源,辦超級大班,謊報生源,違反教學規律辦班等等,導致相當一部分教師連起碼的生活保証都沒有,甚至上訪、停課。
從監利的教育券實驗中可以總結幾點思考:
第一,經濟學家把教育選擇納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設計教育券,在教育內部引入適度的市場機制,打破教師的鐵飯碗,克服公有體制固有的弊端,這對教育效率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但是,完全在市場選擇機制中設計的教育券,卻是一種鼓勵學校之間違背教育規律形成過度競爭的制度,不利於我國現階段基礎教育的健康發展。
第二,我國現有教育資源的分配極不均衡,城市與城市之間、農村與城市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推行教育券並不能改變這種差別,甚至會惡化。現有的師資和設施等也無法公平地體現在教育券的面值裡。
第三,如何發放教育券?是全國統一,還是一省統一,或者是一縣統一呢?無論是哪一種,都無法公平。即使如監利縣以縣為單位統一發放,但在城鎮與鄉村、平原與山區、老學校和新學校之間都無法確保公平。從理論上看,一個農村孩子如得到了一份看似與城市孩子相等的教育券,但是要他去城裡“擇校”讀書,他的實際支出可能要比他得到的那張教育券更多。況且,目前城鎮所謂“優質學校”也已經嚴重超負荷招生,超級大班普遍存在,根本無校可擇。
第四,教育券發放對象的數量難以確定,無法操作。如果按在校學生數發,由於教育券的有價性質,會刺激各個學校在上報學生人數的時候弄虛作假。如果按學齡人口發放,雖然地方政府對家庭人口數量的掌握會相對准確,卻有可能造成教育投資流失,因為學校可能無意關心學生是否就學,而有可能更加關心與教育券持有者達成某種協議,隻求將教育券弄到手以便向政府兌現即可。
我國曾經積極鼓吹推行教育券的學者薛兆豐、吳華和美國學者艾薩克於2005年6月到監利進行了一周的調查,他們將最后得出的結論發表在2005年第6期《教育發展研究》上,其中提到:監利教育券在政策設計的系統性、完整性、徹底性以及政策設計的策略性等方面,都超過了國內所有的教育券實驗。這個方案中止實施的主要原因,除了政治壓力之外,資源約束條件是最主要的因素。
談到教育券,大家首先會舉出浙江省長興縣的例子。其實,長興縣的教育券並不是弗裡德曼意義上的教育券,他們面向的是四種不同類型學校的學生:民辦學校、職業教育、貧困學生、農村技能培訓。這其實是美國學者亨利·萊文介紹的公共教育選擇中的另一種制度安排,即“小型教育券”:學生可以在公辦學校范圍內和范圍外選擇不同類型的教育服務。目前,南京市在學前教育階段實施的教育券撥款方式,也屬於這種類型。
2005年以后,教育界對教育券已經沒有了過去的那種熱情。最近,教育券又被重新提起,實在沒有太大的意義。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