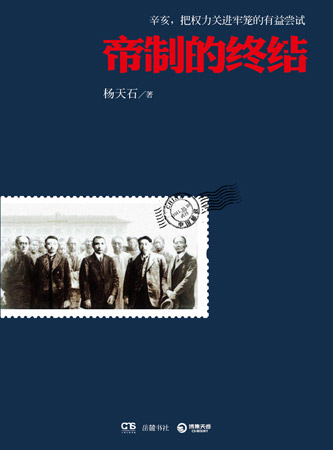
《帝制的終結》 楊天石著 岳麓書社2013年7月出版
原始社會實行氏族民主制,無所謂帝制。帝制,全稱君主專制制度,或稱皇權專制主義,源自原始社會的酋長制。中國傳說中的堯、舜禪讓應該屬於氏族民主制,而夏禹傳子應該是帝制的雛形。公元前221年,出生於趙國邯鄲的三十九歲的嬴政統一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秦帝國。他自稱始皇帝,設想此后的歷史就這樣“二世”“三世”地傳下去,萬世一系,以至永遠。“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帝國雖然二世而亡,此后的中國,朝代不斷更迭,君主專制制度卻一直延續下來,始終是中國的統治制度,延續長達兩千多年。
君主專制制度的特點是:1.皇帝掌握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國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權力都集中到一個沒有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監督的個人身上。因此,社會興衰、國家強弱、民生苦樂,也均系於一人之身。2.實行終身制和以宗法血緣關系為繼承原則的世襲制。皇帝沒有任期,童稚幼兒可以登基,老昧糊涂不須去職。其人不論德或不德、才或不才,即使是痞子、流氓或者低能、弱智,均可按照宗法血統原則承襲。3.以天命論為護符。皇帝又稱天子,宣稱其統治的合法性來自天命,神聖不可侵犯。反對皇帝,那就是逆天,是最大的罪惡和不道。不論是庸君、昏君,甚或暴君,人民都隻能接受、擁戴而無權另擇。因此,君主專制制度是一種十分落后、十分腐朽的制度,它和中國自給自足的地主—小農經濟相結合,構成了我國的中古社會——皇權專制地主小農社會,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封建社會,使中國長期陷於發展緩慢、滯后的狀態。①
然而,這個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卻在1911年被推翻了。那一年,按照中國傳統的紀年,是辛亥年。當年10月10日,爆發武昌起義。從那一刻起,歷史老人突然青春煥發,健步如飛。自武昌新軍打出第一槍起,至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誕生,不過前后80多天,三個月不到。如果從孫中山在異國他鄉成立興中會,提出“振興中華”的偉大口號算起,也不過17年。在一個幅員遼闊、浩瀚無垠的超級大國裡,推翻綿延多年、根深蒂固的君主專制制度卻如此迅速,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凡革命,大都免不了流血、犧牲、破壞。有一種說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動。辛亥革命前,康有為曾經以法國革命為例嚇唬人們說,革命會人頭滾滾,血流成河,伏尸百萬,然而,辛亥革命雖然有流血、有犧牲,但是並不大,社會更沒有大破壞。蘇州反正時,為了表示象征意義,隻命人挑去了巡撫衙門屋頂上的幾片瓦。旋踵之間,制度大變,出現了新舊兩重天的迥異局面。這不能不說也是個奇跡。
辛亥革命之所以勝利快、代價小,原因很多,其原因之一在於滿洲貴族集團的“自作孽,不可活”。
滿洲貴族入主中原,靠殘酷的屠殺與嚴酷的鎮壓建立統治秩序,本來就缺乏正當性與合理性。清朝末年,國勢衰微,政權腐敗,列強入侵,滿洲貴族割地賠款以求苟安,其統治就更加缺乏正當性與合理性。甲午戰敗,維新運動興起,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洲貴族集團鎮壓了維新派,使中國失去了一次改革、奮起的機會。緊接著,義和團運動失敗,八個帝國主義國家聯合入侵,慈禧太后拋棄國都,挾光緒皇帝西逃,這是中國多年未有的奇變。庚子回鑾,滿洲貴族集團創巨痛深,不得不撿起被他們否定過的維新派的改革方案,實行“新政”。客觀地說,這次改革在某些方面邁出的步子更大,是有成績的。例如:廢科舉、興學堂,獎勵實業、鼓勵資產階級發展,編練新軍、實現軍事現代化,以及法制改革的部分內容等。
對“新政”的成績,人們應該承認,但是,不應該夸大。在實行“新政”的過程中,滿洲貴族集團始終拒絕對君主專制制度做實質性的改革。一方面,它派人出洋考察,宣布預備立憲,擺出一副要引進世界先進政治制度的姿態,但是,1908年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1911年成立的“皇族內閣”卻徹底暴露了滿洲貴族集團的虛偽和頑固。
《欽定憲法大綱》宣布:“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皇帝可以頒行法律,發交議案,召集及解散議院,設官制祿,黜陟百司,統率陸海軍,編定軍制,訂立條約,總攬司法,委任審判衙門,集諸般權力於一身﹔對“臣民”則規定了種種“不得置議”“不得干預”的限制。它雖然也照虎畫貓,學著西方憲法,規定“臣民”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自由,但強調必須在“法律范圍”之內,實際上將這些“自由”又取消了。清廷在此前頒布的《集會結社律》中規定,凡“宗旨不正,違犯規則,滋生事端,妨害風俗”者,均在取締之列﹔凡結社、集會、游行等事,民政部、地方督撫、巡警道局、地方官等均可用“維持公安”的理由飭令解散。在《大清報律》中規定,報紙、雜志不得揭載“詆毀宮廷”“淆亂政體”“擾害公安”“敗壞風俗”等類語言,並均須在發行前一日中午12時以前送“該管巡警或地方官署隨時查核”。②可見,清廷制定這些法律並沒有給人民自由,不是在提升和發展“民權”,而是給予清廷官吏管制、取締、鎮壓的最大自由,旨在進一步鞏固滿洲貴族的專制統治。
1909年11月,慈禧太后臨危,在去世之前,搶先毒死光緒皇帝,命令隻有3歲的小兒溥儀即位,由光緒皇帝的親弟弟載灃攝政。載灃攝政后,首先致力於集中軍權,然后,進一步將政治權力集中到滿洲貴族手中。1911年,載灃宣布內閣名單,在13個內閣成員中,漢人僅4人,而滿族大臣則有9人,其中皇族7人,所以當時被稱為“皇族內閣”。清初,滿洲貴族為了拉攏漢人,曾在部分中樞機構實行“均衡滿漢”政策,例如:內閣大學士,規定滿漢各2人﹔協辦大學士,滿漢各1人﹔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尚書,滿漢各1人﹔侍郎4人,滿漢各半。然而到了“皇族內閣”,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
《欽定憲法大綱》的頒布和“皇族內閣” 的成立,表明滿洲貴族集團既不想“讓權於民”,也不想“分權於民”,相反,卻將權力更多地集中到君主個人和一小撮貴族手中。晚清時期,中國出現過立憲派和頗具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他們求穩怕亂,害怕激烈的革命會造成社會的巨大變動和破壞,力圖走君主立憲道路,但是,滿洲貴族集團的倒行逆施讓他們徹底失望。1911年,滿洲貴族集團宣布鐵路國有,與民爭利,這就徹底與廣大人民對立起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興起,幾乎所有的人都站到了革命方面,武昌起義的炮聲一響,立刻風起雲動,全國響應。革命在哪裡發生、何時發生,有其偶然性,但是,在偶然性中,又存在著歷史發展的鐵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成功,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誕生,緊接著6歲的小兒溥儀退位,帝制終結。但是,孫中山很快決定讓位於袁世凱。在讓位成為現實之際,南京臨時政府公布了具有憲法性質的《臨時約法》,這一《約法》樹立了“國民全體”作為“國家主權”擁有者的崇高地位,規定了人民應該享有的各項自由和權利,廢除了絕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最高權力,力圖杜絕官吏有權而人民無權的狀態。它高揚司法獨立和權力制衡的原則,是革命黨人將權力關進牢籠的一次勇敢的、大膽的嘗試。
《臨時約法》的制定和公布本來具有限制袁世凱擴張權力的意圖,但是,單純的紙上法律約束不了野心家,袁世凱很快復辟帝制,企圖重新建立絕對的不受限制的權力。多年來,論者常常以此責難辛亥革命,貶損其價值。然而,殊不知,革命黨人勝利雖快,卻缺乏爭取徹底勝利所需要的力量。定鼎南京后,缺乏北伐所必需的經費,四處借貸,四處碰壁。革命黨人的金庫裡一度隻剩下10塊大洋,不僅無法支付進軍北京所必需的龐大軍費,連維持政府的周轉也艱窘異常。在這種情況下,何能北伐!更何能徹底革命!
當孫中山風塵仆仆,自海外歸國時,就曾制定策略。那時,孫中山的親密助手胡漢民已經出任廣東都督,勸孫留在廣東,練兵北伐,對抗已經掌握清廷軍政大權的袁世凱,然而,孫中山不以為然地說:“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貴族專制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③ 所謂“利用”,就是應許袁世凱,隻要其“反正”,就推舉其為民國大總統。果然,袁世凱為總統的寶座所誘惑,停止進攻革命軍,與革命黨人談判議和。其后,孫中山雖多方籌集經費,准備北伐,直搗北京,以便徹底推翻清帝國統治,為民主、共和奠定堅實基礎,但是,籌款始終沒有進展,孫中山不得不採取此前所定策略,接受和議。不久,清帝即宣布退位。世界歷史上出現了一個“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例子。④ 袁世凱后來雖然背叛了自己的諾言,在1916年當了皇帝,但是,隻當了83天,就在全國人民的反對聲中倒台並且一命嗚呼了,完全應驗了孫中山的“覆之自易”的預言。次年的張勛復辟壽命就更短,隻不過12天。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制度終於確立。從這個意義上說,孫中山是大智者,是最終的勝利者。
孫中山曾經將清朝的司法比喻為希臘神話中國王奧吉亞斯的“牛圈”,養了三千頭牛,三十年中從不打掃,糞穢堆積如山。實際上,中國的專制制度,特別是皇權專制制度也是這樣的“牛圈”。辛亥革命勝利得快,代價小,自然難免有其弊病,這就是孫中山早就說過的:“滿清遺留下之惡劣軍閥、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之勢力依然潛伏,今日不能將此等余毒鏟除,正所謂養癰遺患,將來種種禍患未有窮期,所以正為此憂慮者也。”⑤ 但是,這隻能說明,中國需要打掃和清除的“糞穢”太多,歷史包袱過於沉重,即以君主專制主義而言,它既然綿延兩千余年,又何能在短時期內就鐃歌奏凱,徹底清除其影響和流毒。辛亥革命只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就這一點上來說,它是成功的。我們不能要求它在短時期內完成所有中國革命應該完成的任務。段落不是文章,孫中山和他的同志們一生都在寫一篇大文章。為此,孫中山辛勤奮斗,鞠躬盡瘁,至死方已。他也一直提醒人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紀念辛亥革命,就要繼續寫好這篇大文章。
辛亥百年,辛亥革命研究也已百年,但是,對這次革命的若干基本問題似乎還可以討論。例如,多年來,人們將辛亥革命定義為資產階級革命,其領導力量定為資產階級革命派。但是,對此卻一直缺乏認真的、充分的、強有力的論証,也很少有人要求作出這樣的論証。似乎這是一種無須論証、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實不然。
在西方,推翻君主專制制度本來是資產階級的任務,但是,中國的辛亥革命卻與之不完全相同。第一,這一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對滿洲貴族集團,具有種族斗爭的意義,這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所沒有的﹔第二,這一革命發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列強入侵,中國面臨被瓜分危機,救亡圖存成為第一緊急要務,這也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所沒有的﹔第三,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它面對的是專制制度、封建貴族等敵人,但是,當它革命成功、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之后,很快就發現自己的身后站起一個新的反對者,這就是早期的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中國的革命者有鑒於此,力圖避免資本主義前途,或者取其“善果”,避其“惡果”,節制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並沒有提出強有力的、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在這一方面,他們還趕不上清廷實行的“新政”。關於此點,讀者隻須比較“新政”時期發展資本主義的措施和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多項法令,就不難明白。當然,他們的某些政策,例如,實行“平均地權”,征收單一的地價稅,免除其他稅種,會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當時的革命黨人卻視之為消滅貧富差別、造福全民的良方。我覺得,如果就這次革命過程中所提出的動員口號來說,革命黨人的主觀願望是使革命成為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的三合體,但是,革命黨人所期望的“社會革命”始終未及實行,因此,就這次革命的實際內容來說,是以推翻滿洲貴族為主體的君主專制制度的愛國的民族、民主革命。
關於這次革命的領導,最初的一種說法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領導的,后來干脆省略小資產階級,隻說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了。但遺憾的是,中國資產階級並不為這說法爭氣,放眼辛亥革命史,資產階級熱衷的似乎只是收回利權運動一類的愛國抗爭和立憲運動一類體制內的改革,對體制外的革命並不感興趣,他們寧願跟著康有為、梁啟超和袁世凱跑,而不願意追隨孫中山。有鑒於此,有些學者不得不提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分上層和中下層兩個階層,辛亥革命是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領導的,然而,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也並不支持這種說法。有關史家們說不出這兩個階層是如何劃分的,各自的代表人物是誰,其經濟地位如何影響著他們政治主張的分野。客觀存在的事實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國隻存在一個發展不足、力量微弱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隻支持一種政治主張,走康有為、梁啟超倡導的君主立憲道路。只是在革命即將或已經在全國爆發時,資產階級和“立憲派”的士紳們才逐漸地、部分地轉向革命。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實際上是一批青年學生,包括留學生或者國內新式學堂的學生,也就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中國出現的新型知識分子。據統計,至1905年,僅當時在校的留日學生就有八九千之多﹔而至1910年,國內新式學堂的學生已達一百五十余萬,成為一支很大的社會力量。這批人,和中國社會的傳統知識分子不同,所受的不只是儒家文化的浸染,也不需要通過科舉以謀進身之階。在他們的思想、文化結構裡,既增加了聲、光、化、電等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也增加了西方17世紀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民主主義以至社會主義的成分。他們在校或者離開學校后就成了職業革命家,或者投筆從戎,成為“混”進軍隊的職業軍官和職業士兵,有的則“拿起筆,作刀槍”,成為投身新興文化事業的腦力勞動者,辦報,辦學堂,辦出版社,當記者、教師、文人。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是根據人們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同生產資料的關系,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取得社會財富的方式來劃分階級的。這批革命者大部分尚未進入社會經濟結構,人們根據什麼來為他們劃分階級呢?能根據他們的思想和世界觀嗎?須知,其中有若干人向往“社會主義”,主張“社會革命”呢!早在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就曾訪問設在比利時的第二國際執行局,請求接納他的黨,表示“中國社會主義者要採用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工人不必經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⑥ 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就明確表示,中國不能重走歐美資本主義老路,他說:“近時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跡於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跡者之終無成耶!”⑦ 朱執信在《民報》發表的文章曾大罵資產階級是“掠奪盜賊”,⑧ 后來孫中山也大罵資本家“無良心”,“以壓制平民為本分”,“對於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⑨ 將大罵資本家的思想家定為“資產階級”是不是有點冤?
某次討論會上,一位學者表示:“孫中山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家,難道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果將孫中山定為無產階級革命家,他一定會跳起來反對。”孫中山生前曾表示要當“工人總統”。⑩ 將孫中山定為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會不會跳起來反對,我看不一定,但將他定為資產階級革命家,我估計他一定會跳起來反對。列寧在分析俄國革命時,曾經分析俄國先后出現過的“三代人物”,第一代是十二月黨人和赫爾岑等貴族知識分子,第二代是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民意黨為代表的“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第三代才是“無產階級”。 可見,列寧不曾認為“非無即資”,政治舞台上除了這兩大階級外,沒有其他階級或階層。毛澤東在分析五四運動時也曾認為,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 他並沒有說,五四運動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似乎至今也沒有史學家或其他人對此做過判斷。那麼,我們有什麼充分的理由論定早於五四運動的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呢?
在《民報》和《新民叢報》的辯論中,梁啟超主張實行“制限選舉”,反對給家無足夠儲糧、目不識丁的“貧民”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他看來,如果窮光蛋、大老粗們進了議會和政府,那麼,就“不知議會果復成何議會,而政府果復成何政府”。 革命派與此相反,主張實行沒有任何財產和文化限制的“普通選舉”。反問說,何以家無足夠儲糧,就沒有資格成為議員,“猶是橫目兩足,猶是耳聰目明,獨以缺此區區阿堵故,不得有此權利,吾不知其何理也”。 值得指出的是,孫中山很早就鄙棄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1906年,他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演說時表示:“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絕是歐美所不能及的。”孫中山這裡所說的“國民的國家”,也許可以理解為資產階級的國家,但是,他所說的“歐美所不能及”的“社會的國家”呢?聯系他所提倡的“社會革命”來考察,難道不應該理解為孫中山對一種“破天荒” 的前所未有的政體的追求嗎?1912年,辛亥革命剛剛勝利不久,他一方面肯定美利堅、法蘭西是“共和之先進國”,但是,他同時以極為明確的語言表示:“兩國之政治,操之大資本家之手。”“英美立憲,富人享之,貧者無與焉。” 1915年11月,他致函第二國際,要求派人協助他“把中國建立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到了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孫中山就把他的國家理想表達得更顯豁:“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
在資本問題上,梁啟超歌頌資產階級是“國民經濟之中堅”,認為中國應該“以獎勵資本家為第一義”,為了與外資競爭,應該有大資本家,有托拉斯壟斷集團。革命派則主張實行國家民生主義,將一切操縱國計民生的大企業掌握在國家手中,使國家成為大資本家。他們針鋒相對地提出,不能隻考慮資本家的利益,置其他人的利益於不顧,必須鄭重研究財富分配問題,避免出現歐美社會貧富懸絕、勞動者如在地獄的情況。姑不論今天我們應該如何分析這些爭辯的是非曲直,但這些情況至少可以說明,當時,梁啟超等人是在為資產階級說話,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而革命黨人則是在為廣大人民群眾說話。考慮到當時的革命者追求的是與君主專制相反的“共和”制度,以“平民”自居,自稱所從事的革命為“平民革命”,因此,我認為稱這批革命者為“共和知識分子”或“平民知識分子”較為恰當。
歷史是已經發生過的歷史。歷史學家的任務是還原、重建、說明已經發生過的一切。有一種說法,當時,如果不革命,按照清廷“新政”的路子,或者按照康有為、梁啟超設想的道路走下去,是不是更好?所付出的社會代價是不是會更小?歷史不能假設,我不贊成這一種研究方法。因此,本書隻以辛亥革命的實際發生過程為敘述對象,而不做離開這一過程的猜想式的分析和議論。
我踏入辛亥革命研究這一領域,如果從研究那一時期的文學團體南社算起,斷斷續續,已經有五十多年歷史。如果從參加寫作《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中華民國的創立》算起,也有三十多年了。其間曾比較深入地研究過孫中山思想、新型知識階層的興起、同盟會的內部矛盾、發生於保路運動之后的保界拒約運動、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困難與北伐夭折等專題,寫過若干篇論文,這些論文,大部分已結集為《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發微》一書,后來則收入拙作《楊天石近代史文存》中的《晚清史事》和《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2000年至2001年期間,我還參加過蔡美彪先生主持的《中國通史》第12卷的寫作,負責撰寫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兩章的初稿。這本小書就是在綜合自己的上述研究,又部分吸收前輩和同輩們的成果基礎之上完成的。我的原則是:簡明而不失其要,採擇眾說而又保持自己的獨立見解,盡力發掘尚未被學界利用的新資料,希望以不大的篇幅,全景式地講述辛亥革命的歷史,使讀者能以較少時間全面了解這一革命。我曾經想重讀重要資料,更廣泛地參考海內外諸家的著作,但是,寫作中間插進了一段赴台訪問、講學,歸來后,交稿時間已迫,隻能就這樣見讀者了。亂頭粗服,在所難免,修訂、加工,精益求精,期以異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