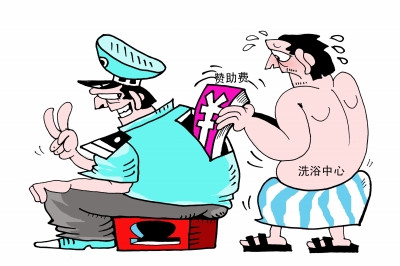怎樣讀書才能取得效果?經驗表明,處理好閱讀中的“入”與“出”是關鍵所在。南宋學者陳善《捫虱新話》雲:“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於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此論道出了讀書的精髓。
閱讀中的“入”,是指對所讀之書全身心融入,潛心對其進行研讀與探索。《文心雕龍·知音》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葉聖陶也認為:“文字是一道橋梁,這邊的橋堍站著讀者,那邊的橋堍站著作者。通過這一道橋梁,讀者才和作者會面,不但會面,而且了解了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這說明閱讀中的“入”,就是讀者通過文字去觸摸作者的內心,與其進行心靈的對話。如此“入書”,方可“見得親切”,實現雙方心情的“契合”。
閱讀雙方該怎樣實現心情“契合”?一個方法是堅持“精思”。朱熹認為:“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爾。”就是說閱讀要慢嚼細咽,通過揣摩語言,達到把握文章內容、體悟作品意蘊與情趣之目的。
在熟讀基礎上精思,確為“入書”之妙訣。蘇軾讀陶淵明《飲酒》詩后寫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蘇軾發現“望”與“見”雖一字之差,但意境全異。何故?蓋因陶詩所表達的是辭官歸田后的喜悅之情,故用“見”字來表達悠然自得之感。若改為“望”,變為主動尋求,就不但破壞了全詩的意境,而且也與陶淵明的節操相悖。蘇軾的體會,表明他對全詩意蘊和詩人的心境都有了深刻認識﹔這種認識若離開了對全詩全身心的“入”,離開反復思索,是無法達到的。
閱讀中的“出”,是指讀者能站在更高層次,對所讀之書做出分析判斷,能從新的角度進行闡發、評價和質疑。哲學家叔本華就主張讀書要與書本拉開距離,不要“入”書過度,要敢於並善於從書本中走出來。這樣讀書,方可避免“是別人在代替我們思想,我們隻不過重復他的思想活動的過程而已”﹔方可在讀后能解其意、識其旨、得其要,真正做到“用得透脫”。明人王驥德《論須讀書》說 “作詩原是讀書人,不用書中一個字”。這話也充滿辯証法,值得揣摩與深思。
魯迅早年讀過不少進化論書籍,曾一度相信社會進化論:“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年。”后來,他在生活中發現了青年們在階級斗爭中分化的事實,“目睹了同是青年,則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身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就這樣,他對這種理論產生了懷疑,並由此發現其諸多偏頗和謬誤。於是,他摒棄了從書本中得到的舊認識、舊觀點,在斗爭中樹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魯迅不囿於書本,敢於突破,敢於超越,提出自己正確的認識和見解。他的這段經歷和思想轉化過程,對於閱讀時怎樣“出”於書,怎樣“用得透脫”,很有啟示意義。
閱讀,要“入”,也要“出”。“入”是“出”的基礎,不“入”則無所謂“出”﹔“出”是“入”的目的,不能“出”就失去閱讀的價值與意義。既能 “入”又能“出”,才是閱讀者必須掌握的秘訣。
《 人民日報 》( 2013年05月28日 24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