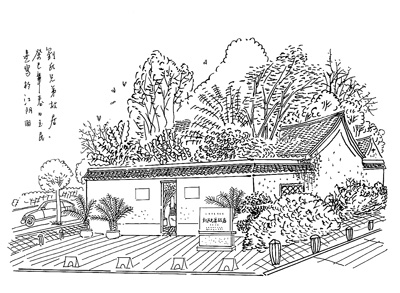 |
|
劉氏兄弟故居正面 |
“天上飄著些微雲,地上吹著些微風。啊!微風吹動了我頭發,教我如何不想她……”
在江蘇江陰劉氏兄弟故居外的石碑上,我讀到了這首經典詩作——《教我如何不想她》。1920年,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新文化運動的主力之一劉半農先生在倫敦留學期間寫下它,后經作曲家趙元任譜曲,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廣為傳唱。石碑上,那個“她”字寫得很大,似乎是在向人們昭示著什麼。過去,漢語裡並沒有“她”字,劉半農首創“她”、“牠”(后簡化成“它”),以區別女性和人以外的事物。從此,我們的語言更多了幾分鮮活的色彩。
“半農圃”、“流芳曲”、“北茂苑”、“音樂橋”……故居外,是一塊美麗的綠島。那掩映在青綠裡的一處處景觀,仿佛是對故居無聲的注釋,敘述著從這裡走出的劉半農、劉天華、劉北茂三兄弟的故事。
“我家的舊居坐落在江陰城內西南隅的西橫街上,街道狹窄,宛如北京的小胡同。舊居系祖上留下來的兩進平房,各帶一個小院落,宅后還有一小片園地。”晚年時的劉北茂回憶起老屋曾經這樣描述。
走進故居,狹小的天井裡,三兄弟的父親劉寶珊親手植下的兩株天竺,一左一右,依舊郁郁蔥蔥。陽光打在樹葉上,明暗相間中透著勃勃生機,時間好像不曾走過一樣。一陣風吹來,葉子隨風晃動,此境此景,讓人倏忽間回到了百年前,歷史又復活了。我仿佛看到,客堂、臥室、私塾、小院、老井、晒醬台、石鼓墩、竹園……處處都有兄弟三人的身影。
偏房被父親劉寶珊改作了私塾,牆上挂著孔子像。置身其中,耳邊隱約傳來劉氏兄弟朗朗的讀書聲。這裡,成為他們最早啟蒙的地方。后面的竹園裡,兒時的兄弟三人常在這裡嬉戲玩耍,多年后,他們仍對這裡念念不忘。1917年,初到北大任教的劉半農還曾寫下《聽雨》一詩,“我到北地已半年,半夜醒來一宵雨,若移此雨到江南,故園新筍添幾許”。他們也常在后院那口老井旁玩,劉半農愛看井,母親擔心他掉下去,常叫他。后來,劉半農一回憶起那口老井,就想起母親——“阿彭快來,你又在看井了!這是母親的聲音。分明是眼前的事,可已過去二十五年了。”
后院有一個長方形的晒醬台,這在江南人家很常見。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革命浪潮很快波及江陰。為向家人表示自己投身革命的決心,劉半農不說話、不吃飯,晚上躺在這方大石板上不回臥室睡覺。這種斗爭精神和愛國熱情終於感動了父親和妻子。是年冬天,他便赴蘇北清江參加了革命軍,實現了投身革命的願望。1917年秋天,劉半農到北大任教,開始新詩寫作,主張詩歌真實地表達思想感情、白話詩在格律上的解放,並大力搜集整理民歌歌謠,創造性地將方言與民歌體引入詩歌創作。“半農先生為人,有一種莫名其妙之‘熱’處。其做事素極認真,其對於學術之興趣極廣博,故彼卒能成為歌謠收集家、語言學家、音樂專家、俗字編輯家,彼之成功,完全由於一‘勤’字……”對劉半農,胡適如此評價。
不知是否因為受到兄長的影響,一個“熱”,一個“勤”,分明也是二弟劉天華的寫照。
白天四處拜師學藝、登門請教,晚上就坐在院子裡老井旁的石鼓墩上拉二胡。劉天華臥室裡,最顯眼的是舊式木床上的那頂蚊帳,它靜靜地挂在那兒——一個盛夏的晚上,有位學生來這裡探訪劉天華,進屋后隻聽見琴聲,卻不見拉琴的人。循聲找去,原來為了躲避蚊虫的干擾,劉天華正躲在蚊帳裡練琴,汗流如注,完全陶醉在琴聲裡。“過去在每天的晚上,一直到很晚,父親總是不停地拉著提琴,或弄別種樂器。在那萬籟無聲的時候,隻有父親的琴聲在空中顫動著,每天總是一樣。”我曾經讀到劉天華女兒劉育和在《父親的琴聲》中的這一段文字。勤學、苦練,於是,《良宵》、《病中吟》、《月夜》、《空山鳥語》……一首首經典二胡名曲,從劉天華的琴弦下流瀉而出。
三弟劉北茂的臥房,小得隻能擺下一張床、一方桌子,少年劉北茂住在這間房。“長兄半農長我12歲,二兄天華長我8歲,他們一個像‘嚴父’、一個像‘慈母’一樣來待我。”在《劉天華音樂生涯:胞弟的回憶》一書中,劉北茂這樣描述兩位哥哥。1927年,劉北茂從燕京大學英文系畢業,在大學從事專業英語課教學以及莎士比亞作品研究。1932年,二哥劉天華英年早逝,為繼承哥哥“改進國樂”的事業,他轉向從事民族音樂的教學、創作實踐和演奏工作,創作了百余首二胡演奏曲,也成為一位民族音樂大師。
三兄弟卓有建樹的背后,是他們對於理想窮盡了一生的熱愛、追求和發奮。一門三杰,可敬可嘆!
從故居的后門走出,高樓迎面扑來,將我的思緒拉回。如今,當年的那條水鄉老街已變成寬闊的馬路,兩條東西向的馬路分別從故居的南北兩側擦身而過,於是,粉牆黛瓦的劉氏兄弟故居便被夾在馬路中間,屹立於周圍現代化高樓的包圍之中。仿佛一種堅守,表達著人們對大師的尊重,更有對文化的敬畏。
池塘上的“音樂橋”,欄杆間鐫刻著的五線譜音符在春日的陽光下閃耀流動,那是劉天華作曲的二胡名曲《光明行》。其實,劉氏兄弟的一生,何嘗不是在向往著光明,追逐著新文化之光?晚年在回憶錄裡,劉北茂評價他的兩位兄長:“長兄把‘數千年來受盡侮辱與蔑視’而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民謠、山歌、農歌、小調、俚曲等民間文學統統比之為‘瓦釜’,他嘲諷那封建文人所偏愛的‘黃鐘’,並勇敢地對其發起了挑戰。這正像二兄天華要‘顧及一般民眾’,而為民族音樂中被‘打在地獄底裡而沒有呻吟機會的瓦釜’——二胡吶喊、奮斗、爭取合法地位一樣。他們兄弟倆分別在文學和音樂不同的領域所做出的開拓性努力,體現了同樣的革新精神。”
忽然間,我想到客堂梁上挂著的冰心先生的題字:“劉氏三杰,江陰之光”。是啊,今天,當我們使用白話文作文,很自然地寫出“她”、“它”的時候,當中國民樂一次次飲譽世界樂壇的時候,“教我如何不想她”——
江之陰,水之南,這座普通的民居裡,走出了中國文化史上三顆閃亮的星。
《 人民日報 》( 2013年05月27日 24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