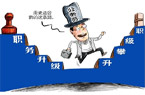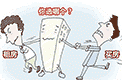曾有朋友聊天說,現在身邊的“奇人”少了。往前幾十年,每每會遇見讓人驚嘆“市井有傳奇”的人物。菜場擺攤的農婦們,張口就是八個音部的合唱﹔鄉野小學的教師,研究著魏晉南北朝歷史﹔路邊閑晃的野漢,竟有一身霸道的橫練功夫……仿佛是《一代宗師》中金樓裡的各色人等,點亮燈后都讓人驚嘆不已。
而余秀華,無疑就是這樣的奇人。近日,這個蝸居於湖北中部農家小院的農婦,因為一首首濃烈而真摯的詩歌備受關注。詩歌之外,身體殘疾帶來的人生艱難,更是成為迅速引爆公眾情感的導火索。
有人說,寫詩其實是在“經歷一種狀態”。沉浸入對自己、對生活、對世界的體驗與思考,方能為詩。在田埂與小院之間,在五谷與三餐之間,余秀華確實是經歷著“詩歌狀態”,這也讓她的人生超越了柴米油鹽。即便有幾分獵奇的成分,即便有一些雞湯的性質,余秀華火起來,也與這樣的人生狀態不無關系。當大部分人都被庸碌的日常包圍著,誰不希望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從這個角度看,關注詩歌狀態中的余秀華,與翻看旅行社打折的消息、給朋友圈裡世界各地的照片點贊,也頗有幾分相似。
很大程度上,詩歌就是“白日夢”。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電視上天天談論著夢想,“我的夢想是讓更多人聽到我唱歌”。沒錯,但又不對。不管屏幕上的技能多麼五花八門,但所謂夢想卻都指向了類似的東西。把夢想等同於名氣,等同於財富與欲望,這本身並沒有錯。但這樣一個單向度的理解,與其說是在堅持夢想、追逐夢想,倒不如說是在消費夢想。正因此,余秀華這樣的夢想家,才有格外的意義。執著於一件事本身,而不是追求附加於其上的東西,把這樣的夢想作為寄生之所、存在之枝,那麼,不管是寫詩還是其他,都已經可說是“詩意地棲居”了。
余秀華之所以被關注、被追捧,正是因為這樣的奇能異士,在我們的生活中已經越來越難以尋覓了。相對記憶中那豐富的社會,眼前舉目盡是鋼筋水泥的森林,隔成小間的辦公桌,為著一樣的指標奔波,躺在沙發上看電視做同一個夢,青春消磨在擁擠的地鐵、重復的流水線上。是的,“痴”,已經越來越難以找到容身之地了。全民娛樂抹平了個人的興趣,快速消費讓功利取代了痴迷,生存壓力更無法承載起無所事事的閑適人生。我們太忙、太累、關注的事情太多,以至於沒有時間去享受一種單純的樂趣,甚至也沒有精力更多地去關注自己的心靈。
余秀華的詩藝究竟如何,可以交給專業人士去評判。但這位女詩人,卻以自己的“異質性”,給出了這樣一個范例: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還有著不同的活法。即便是在再普通不過的小院子裡,也還能找到不同尋常之人、遇到不同尋常之事。在扁平化的時代裡,她提供的與其說是詩歌,是真摯帶來的感動,不如說是一種深度,是關於生命仍然存在無限可能性的驚奇。
余秀華寫道,“我悄無聲息地落在世界上,也將悄無聲息地隱匿於萬物間。”種子也許落入石田,也許落入沃土,但隻要種子不死,就能頑強地發芽生長,為這世界提供一點新的生機。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