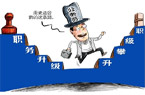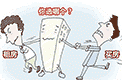余秀華有愛過或者被愛過嗎?那情欲之火,曾經在她生命中炫麗開放過嗎?因為她是腦癱,很多人對她寫詩的體驗產生懷疑。她寫道:“我的殘疾是被鐫刻在瓷瓶上的兩條魚,狹窄的河道裡,背道而行……”細讀,令人惻然:刀砍斧鑿般天生的不幸、別扭的所在、狹小的生存空間,而且無可更改。是的,疾患令她行動不便,也失去打工與求學的可能。農村不能干活的女人形同廢人,婚姻方面由不得她按著心意來。往好處說,她是衣食無憂的,但那亙古的、屬於人的寂寞呢?幸好,她寫詩,她的渴望、欲念、悲傷都以文字的方式釋放。
兩三年前我便知道她,並沒有太多關注。多年來,我接觸過的農村女詩人還是很有一些的。某種意義上,至少一半生來就是文學女青年,小學、初中時哪個不在本子上寫寫畫畫?雨絲、星星、七裡香……但這些不叫詩,叫少女情懷。
命運是在幾時扳的道岔?大概是從有些人上大學,而另一些人去打工或者嫁人開始吧。前者可以親歷她夢幻過、想要過的東西,后者卻像早早開放的梅花,驟然凍結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春雪裡,久久凝固:在忙碌之余,她們認認真真做著文學夢,為自己架空出另一個世界,一個想象中的大觀園。
詩歌這種文學體裁適合大部分農村文學女青年,因為小說需要花更多時間、筆墨去經營人物、結構、情節,這往往太超出她們的日常生活﹔散文要有敏銳的眼光,知道什麼可寫什麼值得寫,而不是見秋葉就感嘆時光易逝﹔戲劇更不現實,她們大部分除了電視劇,很難有機會看到真人出演的舞台劇﹔最后剩下的,就是詩,可長可短,可雅可拙,可在農活之后臨睡之前隨便寫幾筆。
我從不敢說,她們寫得好不好,正如面對余秀華。
《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是好詩嗎?如果是下半身詩人所作,我可能一眼都不看,但因為我知道是一個腦癱女子的作品,我猜想這是她也許到目前為止從未曾實現的綺念。“你”,也許只是網絡上潦亂的幾個名字、瞬息即滅的一封郵件,立刻,沉甸甸的生之分量壓過來,讓夸獎與批評都顯得……那麼荒謬可笑。
而我,隻想說:繼續寫下去吧。世事豈能盡如人意,更殘酷的事也隨時在發生。能抵御歲月、給自己安慰的,不過是文學或藝術。那能歌唱的人,就在黑暗中大聲歌唱﹔那能起舞的,就在舞台上的追光裡獨自起舞﹔隻有一支筆的,比如你比如我,就寫吧,把眼淚、歡笑、絕望、幻想,都用文字吶喊起來。有沒有靈魂都不要緊,會不會被讀到其實也不打緊,隻要把郁結的力量發射出來,每個人都會是一個不再沉默的火山。
(葉傾城)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