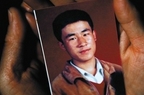站在虎門的威遠炮台四望,南邊是著名的穿鼻洋,西南是橫空而過的虎門大橋,北邊是工商業繁盛的虎門鎮,東邊則是珠江的出海口。我到過不少古戰場,唯在此處感觸最深,不單單是因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更是因為林則徐。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位名臣都不會產生於偶然的一次壯舉,更不會是一時僥幸或因緣際會。
林則徐出生於福建侯官,十四歲考中秀才,二十歲(公元1804年)中舉人,聰穎早慧是不用說了。決定他人生品質的第一階段學習和歷練,是他中舉之后的七年時間。這個人生階段,很像今天的大學應屆畢業生,如何走出書齋面對社會,首先是態度,其次是方法。林則徐初次進京會試失利后,便將謀生與學習擰成一股繩,於嘉慶十一年(1806年),到廈門擔任海防同知書記(近似於今天的科員),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處理洋船貿易。這是林則徐學習政事的開始,也是他成為實干家和一代名臣的開端。
這期間,正是中國與歐美各國貿易戰最膠著的時候。據說林則徐就是在此時學習的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利用工作之便,為自己增長新技能的方法,幾乎是每一個事業有成者的共通經驗。這一點外語能力,促使他日后成為封疆大吏時,常年組織有識之士,翻譯歐美各國的相關資料,以供參考。沒有這種早期的見識和用心,也就沒有日后的成果。后來思想家魏源將林則徐和幕僚們翻譯的文章編輯成書,印行全國,這便是著名的《海國圖志》。這部譯著對清末民初的洋務運動、實業救國和民智啟蒙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入職后不久,林則徐的才能受到福建巡撫張師誠的賞識,將其延聘為幕僚(私人聘請的助手)。進入省級長官的幕府,參與地方事務處理並為長官代寫奏折,是林則徐學習政事的第二階段。奏折是清代各省督撫與朝廷首要的溝通方法,在張師誠身邊的早期訓練為林則徐的筆下功夫打下了扎實基礎。文字工作外,林則徐對海防、軍事、民政和水利諸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特別是在巡撫張師誠剿滅海盜蔡牽的過程中,他參贊其事,增長見聞,經受鍛煉。我一直認為,林則徐應該是在這個階段確立的人生目標,他要成為“治世之能臣”。
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二十七歲的林則徐為自己贏得人生的第一個重要轉折點,他以殿試二甲第四名高中進士。從翰林院庶吉士到江南道監察御使,林則徐十年京官,走的是清貴翰林正常升遷的路子,是他人生的第三個階段。這期間發生了三件事:第一,林則徐這次會考的座師是人稱“父子宰相”的曹文植之子曹振鏞,房師是名儒沈維?。林則徐深得兩位老師的賞識,自此躋身“名門弟子”﹔第二,林則徐加入宣南詩社,結交黃爵滋、龔自珍、魏源等一批思想開放,年輕有為的益友﹔第三,精研水利,著《北直水利書》。總的來講,林則徐這一階段在京城展示了清介的品格、活躍的思想、務實且敏而好學的工作態度,任何公正的上司都會認為他是可造之才和可用之才。
坦率地講,站在虎門炮台上,望著緩緩而去的珠江水,我不由得要想,假如給林則徐換個時代,換個歷史環境,他會不會成為另外一個人?想來想去我也找不出他改變自己的理由。像他這種不間斷自我磨礪,不間斷自我豐富,不間斷擴大良師益友范圍的官員,放到任何時代,他都會脫穎而出,都會走同樣一條“治世之能臣”的道路。
此后,林則徐外放浙江杭嘉湖道台,多次調任升遷至湖廣總督,這個過程是他人生的第四個階段,是展示才能,實踐施政方略,贏得朝廷信任的階段,應該說,他此時已經實現了“治世之能臣”的基本目標。
接下來就是林則徐的人生高潮——廣州禁煙。元明清三代,中國對外貿易一直保持著極高的順差,到清代中葉的時候,中國民間積累了巨額的貨幣與實物財產,便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強國——英國傾銷工業產品套取貴重金屬貨幣的主要目標。中國幾百年來積累的紋銀、西班牙銀元和墨西哥鷹洋,如珠江洪流般涌出國門。這種局面對大清國最直接的經濟影響就是“銀價暴漲”和“銀貴錢賤”,用今天的話講,就是鴉片走私讓大清國同時發生了嚴重的白銀“通貨緊縮”和銅幣“通貨膨脹”,連帶的惡性影響內容繁雜,就不列舉了。
以上種種危害,林則徐在廈門任海防同知書記時已有所了解,但當時走私鴉片數量還不算太多,之后鴉片走私發展到每年三萬余箱,不斷掏空中國的財源。只是,朝廷之中有關嚴厲禁煙與有限禁煙的爭論已經進行了二三十年,雙方爭執不下。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六月,林則徐的朋友,鴻臚寺卿黃爵滋上書奏請“厲禁鴉片,嚴塞漏厄”,並奏陳“禁煙方策六條”。十月,林則徐再次上奏主張嚴禁鴉片,這才有了他的那段“鴉片流毒於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的名言。
就在當下,我曾讀到、聽到一些私議,認為鴉片戰爭的起因是西方列強要求大清國“改革開放”,然大清國見事不明,未能早開放早受益。我從來不認為林則徐是個思想保守的封建官員,他應該是中國當時少有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有識之士,正因為他認清了鴉片走私是貿易戰中的“致命武器”這一點,才會在廣州動用激烈的禁煙手段。因此,如果將“虎門銷煙”僅僅理解為一場禁毒引發的戰爭,或是當成西方列強尋求中國開放貿易的“正常要求”,便是一種狹隘的虛無主義歷史觀。
此刻我站在虎門炮台上,嘗試體會林則徐當年的心情和想法。他被道光皇帝任命為欽差大臣,離京前探望生病的老師沈維?時說:“死生命也,成敗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為門牆辱?”這是師門私語,有孔夫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而他禁煙失敗,充軍伊犁前所作《赴戊登程口佔示家人》詩中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則應該是回顧他站立虎門炮台,眼望穿鼻洋時“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邁和“黃龍未飲心徒赤”的刻骨憂思。
林則徐抵達廣州,視察虎門炮台時,恰好五十五歲。我相信,林則徐應該清楚地知道,他半生平步青雲的宦途,此時迎來了最深刻的考驗,面臨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危局。如果他在道光皇帝駕前沒有展示超人的禁煙決心與才能,而是選擇做一個正常的好官,興修水利,與民休息,平准法度,加上他的見識和洞察力,以及文筆凝練、思想精辟的奏章,還有滿朝眾多良師益友、門生故吏的擁戴,讓他從從一品的湖廣總督,入閣拜相為正一品的大學士,甚至像他的老師曹振鏞一樣畫像入紫光閣,死后入祀賢良祠,應該不會太難。然而,我們絕不能低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官員的節操,正因為林則徐深刻的憂國憂民,不肯逃避責任,勇於擔當,他才主動選擇了這條為官之道中的險途。也正因為如此,虎門成了林則徐從“治世之能臣”轉變為“一代名臣”的節點。
《 人民日報 》( 2014年11月22日 12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