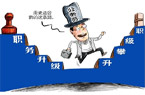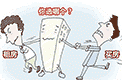有“史上最严”的条例就有“史上最严”的执行吗?如果这两者之间不划等号的话,所谓“史上最严”条例恐怕很快会沦为一个法律泡沫
6月1日零时,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之前,媒体对条例进行了最通俗的解读:凡是“带顶、带盖”的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全都不允许吸烟。
6月1日这一天,有媒体跟随执法人员到北京各处执法,结果“忙碌一上午,市卫生监督员除了一张责令整改通知书之外一无所获”。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果令人欣慰,但并不能消除人们对控烟执法的担忧。
其实,从条例出台的那一天起,很多人就不看好条例的执行。这倒不是人们反对控烟,恰恰相反,如果做一个民调的话,相信会有90%以上的人支持控烟。但是立法容易执法难,有“史上最严”的条例就有“史上最严”的执行吗?如果这两者之间不划等号的话,所谓“史上最严”条例恐怕很快会沦为一个法律泡沫。
人们认为控烟条例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针对个人陋习的执法必然会引发大量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长期普遍地存在,而执法部门又不能坚持长期普遍地执法,那条例很可能会在执行一段时间后“流产”。解决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被执法者,一是执法者。
首先说被执法者。为什么一个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法律会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阻碍,这是因为这部法律规范的是一个道德文明领域中的问题。虽然我们总说,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两者是很难绝对区分开的。
北京颁布控烟条例,从法律上讲是因为中国加入国际公约的要求;从城市形象上讲则是因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需要。也就是说,这是城市文明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速,迅速扩张的城市涌进了大量的人口。目前,中国城市常住人口总量与农村常住人口总量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但是人居住地和身份的改变与人观念的改变肯定不可能同步,人的城市化不仅体现为人在城市中生活,更体现为与城市规则相适应的观念与精神。
城市是人的聚集地,在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近距离的接触必然会造成相互影响和相互冲突。所以,城市文明规则是建立在自身行为和自由不影响并妨碍他人基础上的,用法律语言说,就是个人的权利行使要以他人的权利为边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个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一部分自由,比如控制自己的言行,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大声喧哗,乱丢垃圾,走路、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秩序,接受安检等等。
可能一些人会认为,城市的生活很不自由,但是人的城市化也许恰恰就体现在这些不自由上。人的城市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社会的进步来推动,需要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来共同解读。但从某种意义上讲,遵守法律与规则,体现文明与素养也是人城市化的一个方面。
人们担心一些人不愿意遵守控烟,其实是对当前国人城市化程度和文明程度没有信心。固然人的文明程度要靠教育和培养,但是有时候也要靠倒逼,过度迁就就是保护落后。人都是有惰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步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严厉的执法是推动人迅速城市化的一种重要力量。
其次再说执法者。北京控烟条例实施的第一天,由卫生、工商等多部门联合上岗执法,也就是说,控烟条例的执行主要靠行政执法。而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执法的问题很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一阵风”式执法,风头一过就鸣金收兵,以后再想找人都难了,纵有群众举报,也难以请动那些坐惯了办公室的执法人员;二是多头执法,一个问题好几家单位都有执法权,说是联合执法,但到最后很可能成了相互推诿。
所以,纸上的“史上最严条例”要变成现实中的“史上最严执法”,确实需要下决心克服我们行政执法中的顽疾,条例实施第一天的执法其实只具有宣示性的作用,之后每一天的执法工作才真正体现法律执行的意义和价值。
说到城市的文明,我们总爱拿新加坡举例子,因为新加坡确实是一个以严厉执法推动和倒逼人们文明进步的特殊国家,它没有被动地等待人的自觉与进化,而是以严刑峻法加速这一进步过程,甚至不惜以“恶法”来达到这个目的。虽然中国不能以“恶法”治理社会,但保证法律持续、一体和有效的执行却是应该做到的。
史上最严条例必须辅以史上最严执行,否则我们只能听到一声文明的叹息。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