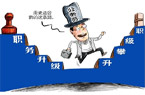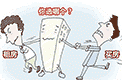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去世。我获悉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83岁也算福寿双全,遂很镇静地寻到此前一篇与特翁有关的文章发微信纪念。那篇文章的题目是《特朗斯特罗姆就像中国诗人的亲戚》,是当年特翁得奖时应《珠江商报》编辑朱佳发之约而作,后来我在李少君接受访谈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记者这么提问“都说特朗斯特罗姆是中国诗人的亲戚,您怎么看”时,不禁心领神会。
可以说,特朗斯特罗姆是继泰戈尔之后与中国诗人关系最为密切的诺奖得主。这首先归功于北岛,他是特朗斯特罗姆的第一个中译者。早在1984年他就化名石默翻译了特朗斯特罗姆六首诗,刊登于该年第4期《世界文学》。在北岛旅居瑞典的艰难时光中,特朗斯特罗姆是他为数不多的瑞典朋友之一,“若没有这些朋友,我早疯了”,北岛如是说——在北岛内心也许有一种特朗斯特罗姆唯我独有的意识也说不定。1985年4月,特朗斯特罗姆第一次来到中国,诗人北岛作陪游览了北京和上海。特翁后来写有一诗,题为《上海的街》,几乎句句警语,近乎真切而残酷地捕捉到了他眼中的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现实,仿佛相面术士一般。细想也不奇怪,特朗斯特罗姆1956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即在该校心理学系任职,其本职工作是一名犯罪心理学家。他的诗作不停留于世象的表层,与此职业不无关系。
第二位加深特翁与中国诗人联系的是李笠。2001年3月,旅居瑞典的中国诗人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在中国出版,成为特翁再次访问中国的契机。当时,特翁已中风坐上轮椅,口齿不清,但这丝毫不影响中国对他的热烈欢迎。在北大举办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朗诵会上,现场挤满了学生和闻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诗人。当时特翁尚未获得诺奖,他对中国诗人的吸引力完全来自作品。
特朗斯特罗姆中国热的第三个原因则是2005年北岛与李笠就特翁的翻译打了一次笔仗。彼时除了他们,至少还有十余位中国著名诗人或撰文肯定或辛勤翻译特翁。当北岛读到李笠的译本时,专门写了一篇《特朗斯特罗姆: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批评李笠“缺乏力度”。李笠也不示弱,撰文《是北岛的“焊”?还是特朗斯特罗姆的“烙”?》进行了行文犀利的反批评。这场“北李之辩”透露了两代译者在诗歌观念和诗歌用字上的取舍差异。相比于精通瑞典语的李笠,北岛根据英译本的翻译的确是“骑在他人身上”。李笠自己的诗歌创作颇见先锋功力,更兼他是直接从瑞典语翻译,无论如何应该更接近特氏本人的语言吧。至于两人的翻译水平孰高孰低,普通读者也难分究竟。
2011年10月,特朗斯特罗姆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诗界对他的推崇与此没有关系。不仅如此,近几年中国诗人隔三岔五远赴瑞典拜访特翁,我知道的就有于坚、王家新、伊沙、蓝蓝、沈奇、莱耳、黄礼孩、冯晏等。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据蓝蓝介绍,特朗斯特罗姆很喜欢中国文化,在家里挂着中国的书法横匾,但有趣的是,他把匾挂反了。当时他们一行人进门看到后,李笠赶忙过去,把匾取下倒过来重新挂好。这个细节折射出了文明与文明之间在进行交流时难免出现的“反”现象。也就是说,一种文明试图输出某种价值观念给另一种文明时,另一种文明接收到的有时却是这种文明想回避的。
“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摆脱令人窒息的旋涡”,这是特朗斯特罗姆最著名的两句诗。现在这位杰出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已经跳出了现实,去往真正的超现实,我们都不知道那个超现实在哪里,但我们终究都要去相聚。 (安琪)
■微语
@老符向阳:有人说,三月是诗人的故乡。还清晰地记得2012年3月24日,在北京三联书店雕刻时光为特翁举办的读书会。
@joey荰洁:重看2005年《上海文学》上所刊马悦然译特翁诗作《巨大的谜语》,译者附记中写特翁中风以后“也继续写诗,他从前是一位很好的钢琴演奏者……他中风后,用左手弹钢琴……世界重要的国际诗歌节争相邀请他,他也喜欢去,由别人代为朗诵他的诗作,他用左手为自己的诗作伴奏。”
@廖伟棠: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也可能是在准确抓住时代精神意义上的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诗人,虽然他的风格如卡尔维诺点出的:可以延伸至未来。但对于芸芸后现代诗人来说,他太超凡脱俗了,后者会用“纯诗”来指称他的努力。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