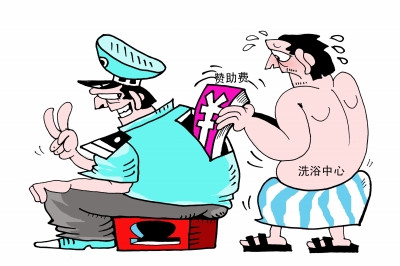|
|
图为迈克尔·舒尔茨导演版《帕西法尔》剧照。 |
自1882年首演以来,瓦格纳的“天鹅之作”《帕西法尔》招致了无穷无尽的批评。有些观点剑指作品浓厚的基督教主题和累赘的宗教教义;有些观点反对骑士高高在上的男权主义;有些对其中唯一一位女性的负面刻画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帕西法尔》赋予无数歌剧迷绝无仅有的审美感知。
在三幕歌剧《帕西法尔》中,无终旋律自《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之后又一次登峰造极。瓦格纳试图用音乐表现出古尔内芒兹在歌词中所唱的“时空易转”的玄妙。现场聆听此剧,音乐给人冰山移动般的感觉,那巨大的恒力之下,一望无际的冰山在缓缓移动但又不易被察觉。人站在冰山之上,似乎还在原地,但已在恒力的作用下漂过千山万水。正如曾执导《尼伯龙根指环》的导演罗伯特·卡森所述,“在瓦格纳中,你的所闻所感只是冰山一角”。
与前作《尼伯龙根指环》或《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不同的是,《帕西法尔》的故事独一无二,讲述的是帕西法尔成为圣杯国王的经历。这一经历围绕着一群高尚纯洁的骑士展开,他们守护着两尊圣物:圣矛和圣杯。歌剧一开始,就交代圣矛落入复仇心切的妖道克林索尔之手。不妨把整部歌剧简单看作如是:圣矛与圣杯分离导致人间混沌无序;帕西法尔英武地将两者完璧归赵,世界重归和谐。
此剧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但真正举足轻重的并非叙事或历史,而是抒情性和超越时空的特质。这一特质也决定了音乐行进,相较于瓦格纳的前作由剧情推动音乐,《帕西法尔》更多是由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推动音乐。第二幕是心理描写最为纷繁复杂之处。帕西法尔来到魔境,受靓丽的花妖引诱,几度动摇后最终坚定立场,发挥神力夺回圣矛并刺死克林索尔,历经磨难,将圣矛物归原主,被加冕为新国王。
首次接触这部歌剧的中国听众,不妨把帕西法尔看作是孙悟空和唐僧的混合体。帕西法尔拥有悟空般的天真和唐僧般的执着,历经美色诱惑试炼,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圆满而归。这是一位大智若愚的能人,有着悟空般的嫉恶如仇和唐僧式的宽宏大量。两则神话都有得救、启迪和得道的思想贯穿其中,主人公慈悲为怀,度己度人。
充实的精神世界和错综复杂的宗教内涵,让《帕西法尔》的舞台制作与音乐一样扑朔迷离。自1882年首演以来,此剧强烈的仪式感和缓慢的心理铺陈成为导演处理的重中之重。剧中最难处理的当属两处“换景音乐”,分别位于首尾两幕的圣餐仪式。瓦格纳为这两段谱写出了历史上少见的雄浑有力的音乐,在顶尖的演奏下能以延绵的声场产生惊心动魄、翻江倒海的效果,这让舞台上的二度创作很难在视觉上与之相称。
现有的制作大多受到1951年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影响。瓦格纳的孙子维兰德·瓦格纳在1951年以超人魄力及才智与现实主义的忠实呈现彻底决裂。在他的导演下,舞台制作彻底摒弃所有在剧本中交代的实景或象征性道具,改用清一色的虚拟背景和复杂的灯光渲染。因为这一开天辟地的改革,1951年后的拜罗伊特音乐节史称“新拜罗伊特”。灯光第一次摆脱演员和布景照明工具的作用,升格为歌剧制作的灵魂。此后出现了两派导演风格,一派模仿维兰德,竭力淡化瓦格纳歌剧中的德意志精神并力行简约;另一派反其道而行之,强化德意志精神甚至到嘲讽地步并制造混乱。后者的极端化例子变为克里斯托弗·施林根希夫2004年在拜罗伊特推出的《帕西法尔》,充满血腥暴力的纳粹场景。
抽象制作的思想显然拥有更多继承者并被主流采纳。维兰德·瓦格纳的弟弟沃尔夫冈·瓦格纳1975和1989年两版、“神鬼导演”戈茨·弗雷德里希1982年《帕西法尔》百周年拜罗伊特版、罗伯特·威尔森1991年汉堡国立歌剧院版、弗朗索瓦·吉拉2013年大都会版等均属此例。歌剧制作蓬勃的想象力和导演诠释的巨大可能性,完全可以超脱对剧情的字面理解,加强了其创作的独立性。这也是《帕西法尔》对现代歌剧制作的重新定义。
在电视纪录片《众说纷纭瓦格纳》中,作曲家郭文景批评瓦格纳的负能量和《帕西法尔》的冗长乏味;老戏骨西蒙·卡洛讲述瓦格纳在《帕西法尔》之后还想写一部佛教歌剧但未能如愿;指挥家丹尼尔·盖蒂提到指挥完《帕西法尔》之后所受的音乐诱惑久久不能散去。《帕西法尔》无论从音乐还是视觉上,都开启了各类艺术通往20世纪大门的无数可能。它的争议性与它的魅力,让人如痴如醉。
《 人民日报 》( 2014年01月16日 24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