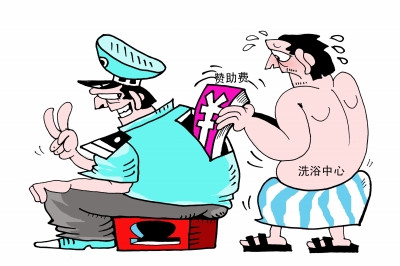图1:《致长官董侯阁下帖》

图2:《江上帖》

图3 宣纸《功甫帖》

图4 油笺纸《功甫帖》

图5

图6
◆ 罗高桦
近日《功甫帖》真伪之争沸沸扬扬。上博专家在事关文化底线的是非上据理发声,是对公众及子孙后代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作为纳税人供养的国有文博机构应有的担当和文化责任感。大众传媒公正客观的报道,充分传达了正反双方意见,体现了职业精神。公众在了解事件过程中也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古代书画鉴赏知识普及教育。
我对《功甫帖》有四点看法,不惮浅陋,公之于众,只图聊补此番争辩之遗缺,并祈教于方家。
【一】 张葱玉、徐邦达未见原作
《张葱玉日记·诗稿》1940年2月4日的日记(第130页)上写到:(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值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茂异》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壁矣。(注:日记原件没有句读)
日记原件没有句读,无法得出张是看到《功甫帖》原作还是影本或照片。从常理来说,怎么可能将《功甫帖》等随信邮寄?
1940年张葱玉年仅26岁,而张葱玉后期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对《功甫帖》缺而不录,而认为“真属双壁”的米芾《苏太简帖》赫然在录。
最有可能葱玉先生在26岁时见到韩慎先寄来的《功甫帖》照片后,一直未曾见到原作,此事便不了了之。
日记观点乃私下日常随笔所记,并非正式对外宣布的成熟观点,考证古代书画时,只可作为参考佐证。仅凭此来确认书画真伪之必然,或辩驳之依据,是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精神的。
而徐邦达先生是否亲见原件,可在1992年《故宫博物院院刊》徐邦达《苏轼·宣德郎刘锡勅草》一文中得到印证,文中:“……曾见赐《苏轼·宣德郎刘锡勅草》一通,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见之《书画鉴影》卷一〇,闻今已分拆,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刘锡勅实非苏笔……”
从以上一段文字可以发现,徐先生已见到《苏米翰札》中的三件,均藏上海博物馆,并“闻今已分拆”,四开中的一开已被分拆、下落不明,这开就是《功甫帖》,徐先生由于记忆有误,误将藏上博的米芾《得书帖》写成了苏轼《功甫帖》,这在2005年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二》第三〇一页、三二三、三二四页得到印证。
第三〇一页:注明:“《功甫帖》楷书,一页,藏处不明。”在第三二三、三二四页提到:“《书画鉴影》著录《苏米翰札》计四帖。东坡行书《刘锡勅》是明人伪笔,不录,《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米芾二帖,一为《得书》,一为《恶札》均真,见下录。”
徐先生在论述《功甫帖》时,并未如鉴定其他几帖那样,明确指明真伪,其对《功甫帖》的评语也是综合了翁方纲与李佐贤的评论并加以引用。
徐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书前序例中,已注明“本书选择记录……也包括一小部见到过极为清晰的照片和影印本。……如要看原件或影印件,则每件大多注明目前收藏处所和曾在何处影印过”。
徐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著录的米芾《得书》、《恶札》二帖,均标明收藏单位为上博,以及详细尺寸。
1953年许汉卿已将册页改装成立轴。至今无任何证据显示(在苏富比图录前)有人对立轴《功甫帖》有过提及和详述。
徐先生在2005年的著作中定为“页”、“藏处不明”,可见徐先生确未见过许汉卿所藏立轴《功甫帖》。
苏富比在图录宣传中给人以张、徐两先生曾见到过原作的假想。
【二】
《功甫帖》与苏轼年龄不符
苏富比专家在图录中写到:“《功甫帖》……当是苏东坡在熙宁四五年间所书,时年三十六七,我们从《功甫帖》雄强润朗的书风来看,视其为东坡中年时期成熟的书作当无不妥。”
根据《宋史》等史籍的记载:“奉议郎”这个官名于宋初置,到太平兴国元年,为避太宗赵光义之讳,改为“奉直郎”,直到元丰三年才恢复原名。其间110余年,宋无“奉议郎”官衔,苏轼在他三十六七岁(熙宁四五年)不会写出这个当时不存在的官名。
贸然认定此帖为三十六七岁所作,可见苏富比专家对苏轼书法风格演变及时代背景并未作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苏轼在熙宁间固然不可能写此帖,但倘若在元丰三年后至元祐前期书写此帖,尚有可能但无证据支撑。
元丰三年(1079年)苏轼遭遇人生重大挫折,因“乌台诗案”,被关押103天,出狱后旋即于正月初一离京师赴流放地黄州。
苏轼这一时期的人生历程,深刻地影响了书法风格的演变。
郭功甫于元丰七年下狱,“5年后直”即元祐四年复官于承议郎,元祐四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如真写过《功甫帖》,应在元祐四年(1089年)以后即苏轼52岁以后尚有可能,但此时书体用笔多取侧势,结体扁平稍肥,信笔挥洒:意忘工拙(图1、图2)。而细观《功甫帖》书体近早期代表作《治平帖》(35岁),从书法到格式非常像集字而成,毫无行笔节奏,字与字之间相互独立,未有贯通之感,也毫无美感。
《功甫帖》非苏富比专家所指三十六七岁所作已成定论。和晚期(元祐后)书风相比更是大相径庭真伪立判,上博专家文中已详述,这里无需赘述。
【三】
油笺纸《功甫帖》是作伪母本
今观《功甫帖》立轴,上面挖镶四件作品于一轴。即1.所谓宣纸《功甫帖》(图3),2.所谓《翁方纲跋文》,3.所谓油笺纸《翁方纲双钩功甫帖》(图4),4.《许汉卿自跋文》。此四件许氏于1953年合装成轴。其中宣纸《功甫帖》、《翁方纲跋文》,钟、单、凌三位先生已在论文中指认为伪作,但未述油笺纸翁氏双钩《功甫帖》真伪。
辨识油笺纸《功甫帖》真伪,对论证宣纸《功甫帖》能起到关键作用。此油笺纸《功甫帖》上钤《覃溪》、《熙斋新购》二印,考《覃溪》印件,印文刀法失准,刻手低下。查《中国书画家印鉴款式》也无此印文,应为杜撰作伪。从许汉卿跋文中考《熙斋新购》印,应为许汉卿所刻,乃因其自认为从英熙斋后人得来。如果去掉这两方印则仅剩油笺纸上九字《功甫帖》。
钟、凌两先生对于“双钩填廓”已详述。要件是从拓本上用油笺纸双钩作为底本,再用宣纸在油笺纸上“双钩填廓”。
许汉卿“可爱”之处是恰恰轻信了书画掮客谎言,将作伪的母本油笺纸双钩底本当作翁方纲双钩本,并为了让这件油笺双钩本有个地方放,特将册页改成立轴。
许氏是民国时天津银行家,爱好收藏,从他自藏有苏东坡印来看,其鉴赏眼力显然不高。
油笺纸《功甫帖》钩摹水平虽逊于《安素轩石刻》,但高于宣纸《功甫帖》,这光从“别”字的最后竖勾就可看出“油笺本”水平高于“宣纸本”了。
油笺纸的《功甫帖》对解开《功甫帖》真伪之谜作用不可忽视。
【四】
《功甫帖》“虫吃”露作伪痕迹
作伪者为了强调年代久远,往往在伪作上做洞冒充被虫吃过的痕迹,方法多种多样,不急于交易的可将伪作置于适宜虫蛀的环境自然生成,此种方法便无法作为鉴定“虫吃”作伪的依据。如急于交易或为掩盖书画瑕疵便人为做“虫吃”,方法不一而足,目的只有一条,即掩人耳目。
细观《功甫帖》满纸有非常不自然、大小一致的小洞,尤其在“苏”字(图5)上有两个很明显的小洞,其位置十分“蹊跷”,应为作伪者有意将双钩出毛病的笔画或不小心晕开的墨痕,用“虫吃”来掩盖,只是手段不高而已。
反观油笺纸“苏”字,却没这两个小圆洞(图6),乃可疑之处。油笺纸双钧于拓本,拓本的“苏”字也无显示有两个小圆洞,(碑帖石刻工匠是严格按照原件来刻字,残破,缺陷等都应照刻,必须严格,无权自改)只有宣纸本(罗纹宣纸)有两个小圆洞。此原因为:由于选用的纸张半生熟或偏生,不慎在填“苏”字时没控制好,发生滋墨,于是人为用小洞来弥补。满纸做两个小洞太显眼,索性随意多做一些,以造成虫吃效果。
结束语
古代书画时隔久远,不似近现代作品的标准件和旁证众多,故切忌匆忙定论,须以质疑的态度来严密考证。旁证和标准件资料有限,不是不可以推理,但推理要符合逻辑性,经得起质疑。作为历史上公认的大书法家,苏轼的书法纵然是信手涂鸦,也不会犯临摹勾勒作伪者的低级错误。其真迹之风神当在拓本和勾勒本之上。
(来源:新民晚报)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