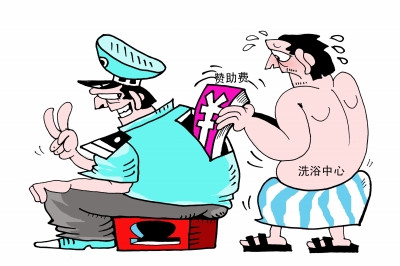一、虚惊
去美国,是9?11后的第三个年头,那时,他们“防恐”的气氛还很紧张,我们一下飞机,就遇上了麻烦。原因很简单,成都美领馆批准我们进入美国的入港处在洛杉矶,而直接飞到纽约的我们,便成了异动者。
翻译小杨怎么解释,也没用。他们过来的人,把我们带去“特别”通道,一一分开,单独盘问。
我们商务团,一行七人,大都不懂英语,面对问话人,几乎都成了“聋哑”。问话人无奈,只好又把我们带去另一个大厅。
进厅门,我就感觉不对劲。四面的玻墙,明晃晃的,站立在两旁的警察,屁股上都吊露着乌亮的手枪。静坐在里边的人,仿佛都在等候柜台上查询电脑的警察们过堂。
“这是啥鬼地方?”我还没回过神,就见两个戴黄手套的巡警过来,强令我身边的一个黑娃开箱。那接受检查的黑娃,两眼发呆地看着箱里掏出的物品,排放在地铺的塑料薄膜上。皮箱已经空了,尽职的文明警察,还不放手,还掏出了弹簧刀。
闯他妈的鬼,我怎么观光到这里来了?原本无所谓的我们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同行的小姜,说出了他的担心:“会不会把我们当恐怖分子?”
我听了想笑。一个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就把当今世上头号霸主吓得如此杯弓蛇影,这日后的世界,真还说不清到底谁怕谁?
我们进厅门全身都被检查过了,鞋袜脱光,连腰间的皮带都被抽出来了,就差没把手提的裤子脱光。
“自由世界”,是法制国家,哪有人们想象的“连空气都是自由”的。不能规范自己行为、缺乏文明素质,尤其像我这样随心所欲的“暴发户”,真正的“自由天堂”,恐怕应该在南非、肯尼亚或者金边。在那里,遇上这样的麻烦,无须我开口,他们都会暗示我怎么解决的。可在这里,我不敢。
“大陆的。”一个举牌的女警用华语在喊。
堂内除了黑人,有色人,就只有我们是黄种人。小姜上去,脸红筋涨地回来,悄声说:“他们在查询我们来美的邀请方,千万记住。”
那公司叫啥?我早忘了,随口说出一个我熟悉的洋名:“是不是香格里拉。”
小姜没敢笑出声,白了我一眼,他像怕别人发现我俩在串供似的,头扭一边。
我明白,这偌大的审视厅,不知暗藏有多少摄像头在窥视我们,而且早就在窥视了。大厅里静得只有脚步声。
小姜上去耽误了好一阵,坐回了原位。而我上去就拿回了自己的护照,那查询电脑的警察连头都没抬。
小姜瞪眼惊异,不知何故。
我也感到奇怪:刚才没进去的团长和翻译小杨,见我出门,还没来得及高兴,竟反被警察请进去了。
等到他们一起出来,我才弄明白。
原来是小姜的手提包出了问题。他提的包是团长的,警察问他包有何物,他不知。警察要他开包检查,上锁的包他又打不开。警察怀疑他是小偷。团长自己前去说明情况,警察仍是摇头。在美国警察看来,自己的包,应该自己提,你的包怎么跑到别人手上去了。
美国警察哪里能懂中国的“国情”——领导的包,从来都是别人拎的。
二、高楼所思
登上帝国大厦,撼人的还是城市“森林”。
昨夜逛曼哈顿,走在大街上,能见的天,是一线天,一幢高过一幢的大厦,笔直如崖,通天的辉煌。而这时登高,一眼望尽的“森林”,却是看不见地了。
你分不清哪里是克莱斯勒大厦,哪里是洛克菲勒中心……华尔街、百老汇湮没在“森林”里。世界金融中心,仿佛就是延向海河、天边的整个城市。据说,眼前所见,大都还是帝国上世纪20年代的旧迹。
我想:那时从“篱笆墙的影子”里走出来的华人,目睹这梦境般的现实,其感受不会亚于13世纪马可?波罗见到的杭州。
倒是无知的我,少年时成天填不饱肚皮,还在高喊打倒“纸老虎”。我们从小谁怕过美帝。可为什么到了今天,国力大增的我们,反倒失去了当年的勇气。
大厦之巅,风很大。横跨新泽西州海河上光照的高吊桥,一条又一条,虹影似的牵起我遐想:一个既无主体民族,立国就两百来年,又在一片荒野——整个曼哈顿仅值24块美金的土地上,何以横空出世,即便是我们现在把它“妖魔化”,它也算人间奇迹。
我绝非崇美者。我老在想,美国走的是什么强国之路?它无需“光荣革命”,也无需“文艺复兴”,直接就坐了世界头等快车,抢占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相形之下,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我们,进入现代社会,反倒是连路都不会走了。
学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学像没有?
“走俄国人的道路”,不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连第一步都走不通。当年,我们与苏联的分歧,不就是国情不同,不可能照搬照学的分歧。
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就如同一个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出生的背景、成长的环境、养成的个性、思维、爱好、习惯等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部精密的机器,“是一个,这个”。我们能研究出别人成功的经验,但谁又能按别人成功的经验复制出自己?这个道理,谁都明白。然而,将其放大,说到国,就理论不清楚了。正如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叙说起别人的成功,头头是道,可他就是没法把他自己说清楚,更没法在社会这个轴坐标中找到他自身的点以及发展的空间。
国与人、大与小,尽管有不同,但走自己的路,在这一点上应该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形成的历史格局、传统文化、思维习俗等等。我们能研究总结出一个国家成功的发展史,但我们能照搬照学吗?“拿来”的东西脱离了它的母体,价值还有多大,能融进我们的母体吗?就像一个人,把别人的大脑、心脏,移植在自己身上,血脉通吗,那还是你吗?
百年的教训,足以让我们清醒,与其多夸夸其谈别人,不如多研究些自己,走出一条让别人来研究我们的路,这恐怕才是我们当代人最该做的。
我们的盛唐,学的是罗马,还是希腊?我们不也成就了世人惊慕的帝国?可那时,又有谁能依样画葫芦,复制出我们那样的帝国?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成功的人明白这个道理,要想成功的国家也同样该明白。
美国,就是自己走出了一条强国之路的典范。不管它立国之初,走“农业立国”的乌托邦道路,还是以后步入世界潮流,走“工商立国”之路,它都是在实践中自我寻找,走自己的路,把世界先进理念结合他们的具体“国情”,走一条自我完善之路。我们学美国,这是根本。如果它立国之初,亦步亦趋地学英国,能成为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当今科技的领头羊吗?
跟我者,必后于我,学像我者,必死于自己。这是很多学艺的家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为什么谈到国,总有些人老想着现存的“拿来”?
双星子大厦是可以“拿来”的,它前年倒塌了,我们来时路过,那里的地面还在清场,看不见的这里,它好像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国体如人体,是拿不来的。国家的国运犹如个人的命运,只能靠自己去把握,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是走不出自己的路的。
离开大厦前,我深感欣慰的是:幸亏,在中国改革开放、泾渭合流的浪潮中,我还没头晕到连自己的路都不会走了。
三、我们差的是胸怀
在美国首都,瞻仰了华盛顿纪念碑,那是169米高的全城之最。城里四处都能看见。
淡黄色的塔碑,高耸蓝天,碑上没有一个文字。
美国人纪念他们200年前的这位老人,什么都没说,说什么都难以言尽。只要你登上过帝国大厦,途经过他们的乡村,还有他们快速称霸世界的当今,还有未来……一切的一切,不都在告诉你,这位美国开国“国父”的伟大吗?
我敬仰他的伟大,不在于他做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做了些什么后的高风亮节。他不以他在“独立战争”中的盖世功名,无视“独立宣言”的神圣。他严拒了有人怂恿他建立军政府的主张,还政于民。他以他的崇高威望主导了"联邦宪法"的诞生,并以身作则,给后来的领导者做出了光辉表率。
一个叱咤风云的始主,功成名就后回归乡野,这是何等的胸怀。中外史上,恐怕都很难找到这样的先例。中国人自来希望有个好皇帝,美国人好就好在有了这样一个“好皇帝”。我只能说,这是他们的福气。
美国人不仅敬仰他们的伟人,同时对那些逆潮流而动的历史人物,也没忘记。
我们在国会大厦的阶梯前,见到两个高大的将军铜像,一个是格兰特将军,一个是罗伯特?李将军。这两个南北战争中的生死冤家,不褒不贬地屹立在民主殿堂外。这就是美国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
没有失败者,就不会有胜利者,一场决定美国命运的内战,是由胜负的双方构成的。如果南方失败的李将军不算人物,那么北方的胜利者格兰特将军也不算英雄,因为这是同胞间不该发生也不可避免的战争。有意思的是,南北双方以刀枪相见开始,以相互尊重言和结束。那不置失败者于死地的战争议和场面,恐怕也是别国的史上难以找见的。他们今天谈论起那场战争,也就少了许多政治色彩。
我记得,当初“联邦宪法”的诞生,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之间的论争,可谓势不两立。“联邦宪法”,是美国走向强盛之路的基石。“联邦宪法”的缔造者、奠基人,写进美国历史的,也包括了反联邦派的首领,他们同样被视为建国之初最杰出的人物。
没有反对方,就没有正确方,至少正确方不会正确得那么完善。以人为鉴,世人都懂的道理,世人未必都能做到。
我还记得,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最早主张的“农业立国”的乌托邦思想,实践证明是错的。历史认识的局限,并没抹杀他最终成为美国至今为止最优秀的四大总统之一。因为他在英国对美国的第二次战争封锁中,清醒地认识到了他的政坛对手“工商立国”的正确,并在总统任期内,不遗余力地把美国的发展方向推向了世界潮流的轨道。
以己为鉴,一个领导者,心中只有国家、人民,才会“王者无私”,才能有如此博大的胸怀。
一个国家,走自己的路,还需要一批有这样胸怀的杰出人物。
美国人有的,我们有吗?
海纳百川,这是美国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