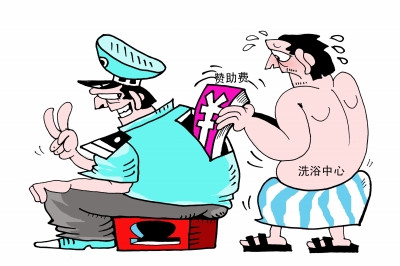现阶段改革体现传承性
曹和平 (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 近期人们普遍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会出台哪些新的改革举措,但回顾近年来改革发展的情况,我们更能看到,现阶段改革具有不少顶层设计思想。这种思想尤其可以从不久前国家将企业注册资本门槛从3万元降低至零这一变化中看出。过去,全球70亿人中有13亿人必须要有3万元注册资本才能开办企业,而其余57亿人无需跨越这个门槛,这会给中国市场和企业家带来什么影响?现在实行低门槛的注册资本,不仅有助于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还相当于政府把企业的“壳资源”还给公众,从而大大动员中国社会潜藏的企业家资源。这种变化无疑将推动中国普通民众获得职业生涯的重大转变,其透露出来的顶层思想的变化是惊人的。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一些人期待现阶段改革会出现石破天惊的东西,但这种想法并不现实。现阶段的改革是前30年改革的全面深化阶段,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接近完成,下一步主要是完善,所以现阶段改革体现的是传承性。近年来我们已经推进了多项改革,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付诸实践,所以接下来端上来的菜和以前不会差多少,但语言表述会更加精致和成熟。
江涌(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尤其是网络虚拟社会当下对改革的期待相当高,但这种被媒体拉起来的期待、被网络舆论吊起来的胃口值得思考。人们应该理性认识改革及其作用,不能坐视社会期待被一些人鼓噪着抬高,因为现在期待越高,未来失望有可能越大,期待不高反而容易有惊喜,喜出望外有助于提高幸福感。当下中国进行改革,并不能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做简单比较。那时社会充溢着一致的“大转型”、“大调整”要求,也罕有利益集团的牵绊,非常容易凝聚人心,现在则几乎不具有那种背景。首先是代际的历史传承,而不是突变,其次是中国社会当前利益分歧很多,共识较少,利益诉求大不一样,过去中国社会在探索改革时很容易找利益的最小公倍数,而现在则只能转而去找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两个数所代表的利益差异很大,反映出在今天的中国进行类似昔日势如破竹的改革几乎不可能。
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
竹立家:当下进行改革的一大背景是:转型中的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这种现状的第一种表现是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第二则是一些公共机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第三是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国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而我们好多专家学者研究问题往往顾左右而言他,脱离现实进行自我“操练”,漠视社会现实和群众要求。最后是主体意识的崛起,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主体身份建构”的时代,中国社会传统的一致性正在向现代的多样性转化,特别是微博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见解。
陈欣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确实在进入某种风险期,但这种风险期主要不是因为政府做错了什么,而是社会自身成长带来的问题。这就好比当孩童逐渐长大,有了一定自主意识但自控能力还不足时,容易闯祸惹事;而当孩童真正长大,完全独立自主时,家长不仅不能随意干涉,反而会对孩子逐渐产生依赖性。因此,中国之所以步入风险期,就是因为自己在某些物质领域的积累虽然达到了一定的丰富程度,但是社会成熟度还不足,就好比一个少年,虽然已经拥有一米九的身高,但是年龄还只有十二三岁。整个社会都需要不断在改革进程中历练才能早日度过这个风险期。
曹和平:农村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房价之所以高,并不只是和地方政府、房地产商有关,而是存在农村土地制度这一制度性因素。中国现有人口中,基本是一半在城市,一半在农村,但是农村的小产权房不能在大市场范围内交易,因而通过购买农村住房不能实现保值增值目的。因此,与不断上涨的城市房价相比,农村房价很难提高,农民取得的货币收入很难通过购买农村住房实现升值,所以农村居民选择到城市里买房子。这就在制度上不断抬升房价,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风险。
中国众多普通百姓收入低的主要原因就是除了工资性收入外,他们获得资本性收入的途径非常少。未来要进行生产要素方面的改革,就应考虑留个口子,使农民既有进城打工的劳动收入,又能在农村获得资本性收入。如在征地补偿上,既要考虑让农民获得货币资本,也要设法让他们能从征地上建设的各种工业园区、项目中获得股权资本,从而更好地帮助农民获取当今和未来的收入。
江涌: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当下进行改革就是要和国际接轨,要接受国际秩序,而接轨的表现就是全面市场化,包括所谓国有资产资本化,我认为这种思路需要慎重,否则会带来很大风险。市场化就是资本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市场化则可能成为国际资本化,而国际资本化就是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一类帝国主义)来改造中国的生产方式,改造中国的经济、社会与国家。从上世纪拉美国家的资本化经验来看,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路线是走不通的,只能变成事实上的附庸,我们必须要对其蕴藏的巨大社会风险加强警惕。很多时候,不是细节决定成败,而是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只是影响好坏。
以开放促改革
陈欣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多年,其中存在各种微妙变化。例如,在1978年到1988年间,中国更多是以改革带动开放,因为那时如果不进行改革根本就无法顺利实现对外开放;但在1992年以后,则主要是以开放促进改革,这时如果不继续进行开放,就无法真正融入世界。改革进程中存在的一个难点就是,假如中国是个封闭的系统,内部的改革阻力如果大于动力,就很可能改不动,但如果进行开放,就会改变内部力量的对比,给改革增加新的动力和推力。因此,我们除了要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推进开放外,还要在法律制度改革、立法和行政改革等方面同样以开放促改革。
江涌:在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市场化”并不是改革一以贯之的。有些媒体关注改革时很大程度上在强调市场化,这有点过,不能把思想纠结于要么市场、要么政府,两者其实并不构成矛盾关系。我们应该看到,除了市场(企业)和政府(国家)外,还有社会。众多东亚国家的治理经验和中国国情决定中国不能走“小政府,大市场”的路子,而是要“强政府”。我们看到,近期政府的简政放权举措中涉及十分广泛,在多项审批权下放的具体举措中,有的是要推进市场化,有一部分则是大力发展社会化,还有一部分是要强化政府职能。总的来说,改革取向市场化不是唯一的,还有社会化和国家化。
竹立家: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深层结构上呈现“结构性紧张”。这种紧张既包括“利益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和“价值结构的紧张”,还包括“制度结构紧张”,其主要特征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不相适应的状况比较突出,但由于经济学的霸权主义,经济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间的冲突比较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向深层次挺进。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社会重新嵌入公平基因,过去可以经济为中心构筑改革话语,未来必须以公正为中心,打造改革的结构性升级版。我们的改革应包括价值高度,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很多措施只讲现实利益,不考虑社会价值,应像资本主义世界把自由作为核心价值一样,把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打造公正的秩序和社会体制。
曹和平:我同样期待下一步改革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新亮点,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理论改革应该有更多的国际视野。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没有硬实力,很容易被别人打垮,但如果没有软实力,别人不打,自己就会先垮,中国必须在软实力传播上实现重大突破。同时,中国还要正视过去在科技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一些重大科技工程中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通过改革让真正爱做研究的人做研究,而不是让那些爱钱的人做研究。
只要稳步推动全面改革,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中国到2017年就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或与其持平。中国现在已经拥有近两万个各类科技和产业园区,即使成功率仅有2%,也有约400个成功园区,每年还有近800万大学毕业生成为新增劳动力,而美国每年只有160多万大学毕业生。可以说,到2025年,如果美国没有50个硅谷,没有5亿的人口规模,将很难与中国竞争。要真正促成这种竞争变局的出现,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围绕改革开放不断奋斗。▲(本文节选自环球时报举办的座谈会嘉宾发言,林鹏飞、曹磊整理。)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