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切实完善和贯彻落实前置性制度规范,才是给予婴幼儿全方位、深层次保护的应然举措
近日,媒体连续报道了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以婴儿 “患有先天性疾病”为由,通过劝说产妇家人放弃婴儿,私自将孩子抱走“处理”一事。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现在,媒体多称该案为“盗卖”婴儿事件。在我国刑法中,“偷盗婴幼儿”的行为可能涉及四个罪名:以出卖为目的的拐卖儿童罪;以收养、奴役为目的的拐骗儿童罪;以索取债务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根据已经曝光的案件事实,当事医生张某以营利为目的,劝说产妇家人放弃所谓患病婴儿,并以秘密的方式将婴儿卖给跨省贩婴集团。这种“盗卖”行为已经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第240条的规定,具备拐卖儿童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与此同时,2010年3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中指出:“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贩卖给他人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据此,张某的行为理应构成拐卖儿童罪。
拐卖人口犯罪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人身权利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将新生儿作为商品随意拐骗出卖,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新生儿的人身权利,同时也必然会对新生儿的家庭关系造成极大损害,甚至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笔者认为,本起“盗卖”婴儿案件之所以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完全是因为本案的行为主体具有特殊身份。众所周知,医生具有救死扶伤的职责,作为迎接新生命的产科医生,更是使命崇高的“白衣天使”。然而,本案中的张某却从“白衣天使”转变成为贩卖新生儿的“黑衣魔鬼”,这一角色分裂的背后,折射出张某的人性畸变和职业伦理的堕落,更反映出产科医务人员一旦实施拐卖儿童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会更大、更严重。
依笔者之见,本案在刑法上的评价似乎不具有太大的争议,但是本案所反映出的问题却令人深思。笔者了解到,在一些大医院,医护人员即使要将医院的仪器设备携带出院,也需要履行相应的管理程序。而对于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相关管理规定更是非常严格。例如,新生儿出生后会马上戴上“腕条”或“脚条”,写上母亲的名字;新生儿从产房到产妇住院楼层的交接都有规定的程序;新生儿做检查和注射疫苗等都要有家属的全程陪同。这样严格的规定,既是出于保证婴儿人身安全的考虑,也在于明确医院和产妇家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然而,这些制度在涉案妇幼保健院却并不存在,相关管理规定和执行流程的缺失,导致张某能够轻易地“盗卖”新生儿。
刑法作为后置性的法律规范,更多是承担事后救济的角色,而作为日常医护管理的前置性制度规范,理应更多地承担起事前预防的责任。痛定思痛,为了有效预防和杜绝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切实完善和贯彻落实前置性制度规范,才是给予婴幼儿全方位、深层次保护的应然举措。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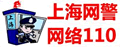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