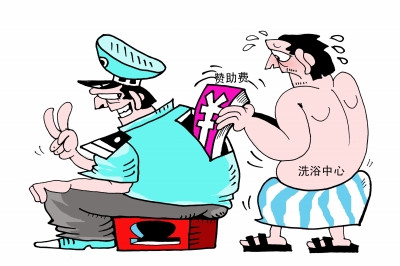当孙犁还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所有研究工作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的视角和进展是阶段性的、侧面的、随机的。当作家告别人世,研究者更能全方位地“接近”研究对象,作出先前不敢作出的结论,说出先前不便说的话。不再“说话”的孙犁,用纯粹的文学创作活动,展示了他可贵的文化生命。
孙犁和鲁迅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研究者已提出了孙犁和鲁迅的关系,有的论点明确说孙犁是鲁迅的继承人。在这个命题底下,是一篇大文章。鲁迅活着时,追随他的文化人很多,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也不能概括当年“鲁迅风”的强劲。从文学史看,有的作家甚至自命为鲁迅的弟子,为鲁迅弘法,似乎得了先生的衣钵真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只说他们是早年亲近先生的人,而不是先生的继承人。为什么与先生无一面之缘,从未直接交往的孙犁竟成了鲁迅的继承者?论据有三。一是孙犁由“五四”后的新文学启蒙,自认鲁迅为精神上的导师,把鲁迅的作品当成研修文学的范本,并把鲁迅当作人格楷模。当孙犁还是一个文学少年时,就关注世道人心,将文学和民族的命运相联系。鲁迅挺直了的脊梁、不屈的灵魂,使少年孙犁产生崇敬感,亲和感。又因为他与上海时期的鲁迅没有直接交往,超脱于各种争论之外,他和鲁迅的文学血缘关系就显得更纯粹,没有沾染私人意气和团体偏好。抗战爆发后,孙犁以文化战士的身份,自觉在反法西斯的战场上宣传鲁迅,歌颂鲁迅,把一个文化巨人当作中国不会失败,民族不会灭亡的象征。同时,他又以个人的创作,以笔作枪,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用诗情画意展现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侵略者面前的坚强和勇敢。枪林弹雨穿不透“苇子的长城”,铁蹄炮火毁灭不了一望无际的荷花淀……二是孙犁对鲁迅的继承,不仅早年学习鲁迅的作品,还表现在他一生虔诚学习鲁迅曾经学习过的作品。他购书的一条主要线索,是鲁迅日记附的书账书目。20世纪70年代末,沉寂近20年的孙犁在海河之滨说话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孙犁在当代文学史上发出的声音,不单是一个个体作家的重操旧业,“二次解放”,老兵新传,孙犁在率领文坛的一支生力军。三是像鲁迅一样,孙犁身上凝聚了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他的博览群书,从文化遗产的源头活水汲取营养,既延长了个人的文学生命,又弘扬了民族的文化之光。孙犁生活的时代,旧文化保守势力已销声匿迹,孙犁和同时代的人,有条件客观公正地面对文化遗产。尤其是频繁的政治运动,更使弘扬传统文化显得及时和重要。
孙犁和巴金
孙犁一直视巴金为前辈作家,他们之间也没有直接交往。两位文学老人是相互尊重、文心相通的。上世纪80年代初,巴金在香港报纸开设专栏,沉痛地反思“文革”,用真话为当代思想界、文学界开路,影响巨大。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一文中,巴金引用孙犁《远的怀念》一段话,显示了两位文学老人对十年动乱的共同批判立场。孙犁的《芸斋小说》,还有不少犀利的杂文,对十年“文革”发出控诉和揭露,毫不留情。与巴老不同的是,孙犁主要是以文学的形式,隐晦的手法,暴露他的亲历亲见,揭示动乱中各式各样扭曲了的人性。巴老一直自谦他“不是文学家”,最早投身文学事业,就声明是用文学来战斗,战胜黑暗,迎来光明,用文学实现人生的理想。这种文学观,也在他的《随想录》的写作中贯穿始终。孙犁则自觉要当文学家,强调作品的文学性,重视作品的生命力。与鲁迅的早期小说一样,孙犁在新时期的创作,也是在剖析国民品性,呼唤真善美的回归。继承文化遗产,不只是接受典籍,还展现前贤的人格光辉。《觅哲生》不足千字,在孙犁作品中不占重要位置,但这篇短文却说尽了他的全部心事。孙犁的根本烦恼,最大的痛苦,就是真诚的丧失,所有人性美在政治动乱中的失落。所以,他用回忆满足自己的精神所需,让消失的真善美在心中回放。他用纯粹的文学形式说真话,并且不满足于只说真话,使他和巴老成了当代文学的良心。他和巴老的可贵,就在于:为了忠于自己的信念,决不因风吹草动而动摇。当有研究者将孙犁和巴金作比较时,孙犁谦虚地说:巴金那样的作家,我们比不了。
孙犁与新时期文学
文学界对孙犁的重新认识,是在十年动乱以后,可以拉出一个很长的名单来,证明不少作家对孙犁的尊敬和佩服。从文学作品的生命力看,孙犁数量不多的小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新进作家学习的范本。孙犁的活法,孙犁农夫般的劳动姿态,不凑热闹、不求闻达、不以名位追求私利的情操,更成了文学界一道独特的风景。30年间,孙犁的人格和作品的双重魅力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整个文学界有了一个参照。而孙犁为当代文学击鼓助威、提携新人、评介新作,为整个文学事业的兴盛而欢呼,同样可以拉出一个很长的名单来,证明在孙犁的鼓励下,有许多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壮大了我们的文学队伍。
当代文学蓬勃发展,盛况空前,孙犁有很大的功绩。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