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品鑒:《潛行者》,行在鏡中猶不知
 |
|
電影《潛行者》劇照。 |
蘇聯著名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借由本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展映被更多的中國觀眾認識。他如鏡入夢自在游走的電影語言,得到過英格瑪·伯格曼的高度評價。盡管隻有七部半作品,他卻創造了一套獨特而豐富的電影語匯。一方面,他的影像著迷於捕捉生命感受,索跡心靈危機,影像的真實質感“如倒映,如夢境”直抵人心。另一方面,他視電影藝術如信仰,如音樂與詩,且琢且磨,不可褻玩。他執著地將電影提到電影的高度,至少達到了一個目的,將把電影視為工業與商業范疇的一干人(從業者、准從業者及相應觀眾)及時勸離,互不相欠。這對於當下燥熱難耐的中國電影界,大概是不可想象的。
《潛行者》是塔氏在蘇聯電影體制內完成的最后一部電影,歷經三年多,三易攝影師。電影講述了潛行者引領科學家和作家穿越一片有著千變萬化的陷阱的“區”,去尋找可滿足人們意願和欲望的神秘房間。他的上一部影片《鏡子》因“看不懂”而飽受爭議,以至於《潛行者》在眾多劇本被拒后的三年才得以拍攝。即便如此,根據科幻小說改編的《潛行者》,不僅完全割舍了奇幻、情節性和冒險趣味,更是放緩了剪輯頻率。他堅持電影與觀眾的溝通方式,認為若一味迎合大眾品味,就隻不過是為了搜括他們的錢財。
比之結構紛雜、語言瑰麗的《鏡子》,《潛行者》開啟了塔式創作的簡約路線,並遵循時間、場景和行為的三一律原則。沉溺於《潛行者》荒寂的末世景觀,你既能察覺多位大師的身影:維果的日常詩意、布萊鬆的苦行、帕拉杰諾夫的神秘、伯格曼的鏡像、安東尼奧尼的游蕩,更會著迷於塔氏影像的獨具魅力。樹、荒廢的房子、積水的地面、起霧的水塘、跳脫尾隨的狗、忽現忽滅的落鳥、無處不在的布谷聲、叮咚不斷的水滴、剝落的牆皮、空屋中的鏡像、憂郁的女人、無辜的女孩,他們不在劇情(小說)中,隻在詩(記憶、夢和幻想)中,並再一次完成塔氏影像對時間的顛覆。
在《潛行者》中,塔氏關於過去和現在、想象和現實的平行結構已經無須存在,他執迷於挖掘的“死寂”氛圍終於找到一個最適合托起的場域——禁“區”。他賦予“區”全新的鏡像價值,以令“死寂”時刻得到無限包容,並凝聚時間的所有刻段。如果說薩特在《伊萬的童年》裡發現的“死寂”是戰爭,那麼在《潛行者》中就是這片非地。它既在現實之內,又超越現實、跨越現實,任由潛行者為它建立規則。它被隔絕在現實社會之外,潛行者定義它是非邏輯、可感知、容納道德的,是惡念者的絞肉機,隻有好人才可以抵達它的核心——神秘房間,並在祈求中獲得幸福和心靈救贖。禁“區”激活了塔氏影像中神秘靈動的自然景觀(雨、霧、鳥鳴、狗、魚等),也打通了已被人類拋棄的文明(聖像畫、手槍、電話、硬幣等)。這個極富鏡像色彩的禁“區”與其說引向未來,莫若說指向對人心過去全部時刻的審判。
與潛行者同行進入禁區的二人,一個是科學家,一個是作家。潛行者作為介於“白痴”和“瘋子”之間的理想主義者,堅忍苦行。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冷戰威脅的陰影下,潛行者有如一個相信人類會因為缺乏靈性生活而滅亡的先知。電影尾聲,三個人終於來到神秘房間的近前,作家卻望而卻步,原想炸掉一切的科學家也拆掉雷管。面對房間,他們喪失了所有的勇氣與意願,他們顯示出的虛弱與貧瘠的靈魂,讓潛行者絕望哭泣。
在這個為潛行者構建的禁“區”中,最后一個鏡頭來自神秘“房間”的視角,審視鏡頭盡處三個背對背坐在地上的頹喪者。房間地面的大片積水佔據鏡前大幅畫面,房間驟然落雨,漸而收起。遠景陰影中的三人在雨光倒影的閃爍變幻中靜默著,地面的水光裡布滿被遺棄的零件,一尾大魚在黑色液汁中游弋。這時,一段由銅管樂吹奏的《波萊羅》令人不安地響起。
塔可夫斯基承認,影片中的三個角色都代表他與世界的一部分關系,但顯然潛行者和他創造的“區”,才是他真正要傳達的主題:道德拯救。此后他攝制於意大利的《鄉愁》和瑞典的《犧牲》更加明確地繼承了這一主題。如果說1957年蘇聯瑪雅卡工廠的核災難觸動了塔科夫斯基拍攝《潛行者》,那麼影片《潛行者》就是對7年后震驚世界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預言。
《 人民日報 》( 2016年05月19日 24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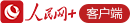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