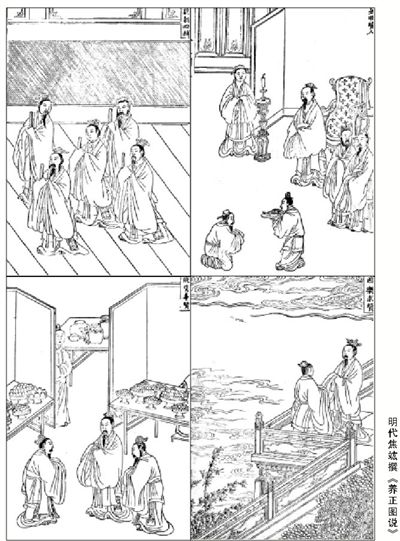
“治國經邦,人才為急”,古今治理,都把人才放在首位,所謂“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然而,人才的標准是什麼?人們常常說要“德才兼備”,把德與才作為用人的兩個重要參數,那古人是如何把握德與才的尺度的?
重德始終是用人底線
司馬光言,“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古代君主用人,多取德才兼備。考諸歷史可以看出,在天下紛亂時,往往更看重才干。而國家安定時,對德行的重視度就大幅提升。在非常時期,一些有為的雄主用人的時候,迫於人才緊缺的形勢,也會提出“唯才是舉”的主張。但是,唯才是舉絕不是忽視德行。
作為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在糾合諸侯以伐宋的途中,遇見賢才寧戚,就想用他。面對臣子的勸阻,桓公說出了一番發人深省的話,《呂氏春秋》記載了這一段故事。其臣說,寧戚是衛人,不如派人去打聽一下他的口碑,“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說:“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顯然,齊桓公採取的是“唯才是舉”的策略。這種用人思路,吸引了管仲、寧戚等一批大才輔佐,成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業。
春秋戰國時期,人才就是競爭力,各國爭相求才,如何用人,彰顯的是君主的胸襟氣度。然而,即便放寬用人標准,“專取其才,不考其行”,也決不是沒有底線。
魏文侯之用樂羊,清晰表明,人才一旦突破德行底線,就無人敢用。
當初,魏文侯用樂羊而不疑,用之攻中山國,樂羊之子樂舒就在中山為官。文侯左右本就妒忌樂羊驟得大用,見其總是不攻,便在文侯面前說他的壞話。但文侯把群臣的告狀信都封在篋內,在樂羊攻下中山后,文侯為之設宴慶賀,宴畢送他兩個箱子的告狀信。
然而,文侯的疑心也便在樂羊攻中山國之時種下了。當時,中山子姬窟把樂舒烹成羹送給樂羊,想以此使樂羊悲慟而不能戰,沒想到樂羊夠狠,直接就在使者面前吃了一杯。文侯對睹師贊說:“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很有點感激感動的意思。但睹師贊卻說:“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這和管仲懷疑易牙“人情莫愛於子,其子且忍之,何有於君”之論是一個道理。
一語警醒了魏文侯,文侯在慶功宴后,封樂羊為靈壽君而罷其兵權。《戰國策》寫道:“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正所謂“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又“虎毒不食子”,連自己的親骨肉都敢吃、都敢烹給國君吃,如此無底線,無基本的“人性”,古代雄主“疑其心”也是必然。
典型的例子還有三國時期的呂布。呂布有萬夫不當之勇,但其德行有虧,最要命的就在於他一會兒投奔這個,一會兒投奔那個,最終無人敢用而淪為曹操刀下之鬼。
貞觀六年即632年,太宗對魏征說:“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這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用人導向問題。而魏征之答,道出的正是用人標准變化的原因:“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為何德的標准會因勢而變?
在紛爭時代,唯才是舉。原因在於,才在“破”上極為關鍵,誰得大才誰就可能使國富民強,甚至扭轉乾坤、贏得天下,而重才產生的用人導向,更能吸引天下有才者歸之。而在承平時期,就必須德才兼備方能任用。這時,正所謂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治國需講究“烹小鮮”的功夫,此時即便大才也往往隻有慢火徐圖之功,而無立竿見影之效。社會對德的要求也變得更高,正所謂“上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德若不佳,則會產生極大破壞效應,影響社會風氣,甚至影響為政的公信力。若重才不重德,則一面“立”而一面“破”,無異於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唯重德才兼備則皆致力於“立”,方能致善治。同時,更產生強烈的用人導向,使賢人近、小人遠。
在德與才的問題上,康熙見識亦很深刻。他認為:“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1687年,康熙對吏部說:“朕聽政有年,見人或自恃有才,輒專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優為佳。若止才優於德,終無補於治理耳。”顯然,康熙著眼的還是承平時的治理而非紛亂時的虎爭,其結論也正是在治理實踐中得出來的。
以德為先重在知人善任
有人說:“對人的道德進行量化評價,是一個管理學上的世界難題。”原因就在於,與才干的“外秀”相比,德更傾向於“內秀”。德雖然也有外在表現,但有時未必能真切彰顯德的本質。同時,德不在於一時,如白居易詩“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勁草是否名副其實,唯有疾風可知﹔臣子是否真正忠誠,局勢危難之“板蕩”能識。然而,真到關鍵時刻,雖然能識忠奸,隻怕一切都晚了。
這個關鍵時刻,德比才更為重要。古代君主識人能否高出一籌,關鍵就在對這個德比一般人更能洞察幽微,更有遠見卓識。沒這等功夫,往往就會游移不定、遲疑不決。相反,就會氣定神閑、泰然自若。
戰國時期的齊威王在知人上就很有一套。
據《戰國策》載,當時,秦國通過韓、魏去打齊國,齊威王派章子為將應戰。章子與秦軍對陣,居然搞得軍使來往頻繁,大有結盟友好之勢。章子甚至還把軍旗換成秦軍的樣子,卻暗地裡派部分將士混入秦軍。當然,這番良苦用心的計謀,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一些不明就裡的人,馬上就說他叛齊了。連續三次都有探子如此這般的報告,但威王始終沒有反應。當時就有朝臣急了,請求發兵攻打章子。齊威王說:“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擊之?”
面對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的情勢,齊威王仍然無動於衷,堅定信任章子。不久捷報傳來,齊兵大勝,秦軍大敗,秦惠王隻好自稱西藩之臣,派特使向齊國謝罪請和。威王左右侍臣想弄明白,威王怎麼就知道章子絕對不降秦。齊威王便說了一段往事,足見其察於平時、知於細微。
齊威王說,章子的母親啟死后葬在馬棚下,我任命章子為將軍時,勉勵他說,先生的能力很強,過幾天全兵而還時,一定改葬將軍的母親。當時章子說,母親生前得罪了父親,臣父不允許臣改葬就死了,假如臣得不到父親允許而改葬母親,“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威王的結論是:“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以今天的眼光看,很難說章子對待父母的態度是正確的。當然,歷史地看,章子謹守的是當時的基本道德倫理,以此為底線而不敢有違。威王也正是從“人性”的角度去考察的,他的判斷是,能恪守基本道德倫理的人,德行怎麼會差呢?
必須看到,如果隻用日常生活中的這等細行,來決定干部任免,恐怕也會失之偏頗。探索日常德行的細化、量化考核,這種嘗試是有意義的,作為參考大有裨益,德考分過低值得警覺。但另一方面,若以此為硬杠杠,恐怕也多少會存在一些問題,幾分之差可能很難說明前者就一定比后者德行差。
德考的方法與機制
在一定程度上,古人以問之於民、用人導向和事后懲處等辦法,解決德考量化的難題。
雖然德考量化容易存在誤判,但品行不佳之人,自有公論。康熙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路。他說“凡居官賢否,惟輿論不爽,果其賢也,問之於民,民自極口頌之﹔如其不賢,問之於民,民必含糊應之。官之賢否,於此立辨矣。”意謂知人賢否,不能僅靠輿論或身邊人的褒貶,更要問之於民。民眾的“極口頌之”與“含糊應之”,在今天看來都極有現實意義。當然,難點就在於能否聽到百姓的真話。
康熙還強調用人上的懲惡揚善,兩手都要硬:“昔人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舉賢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廢。如但舉賢而不退不肖,則賢者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懲,終非勸眾之道。唯黜退不肖之員,則眾人方知所戒,俱勉為好官矣。”用今天的視角看,舉賢,就是樹立一個標杆,讓大家見賢思齊﹔退不肖,就是構筑一個底線、紅線,讓大家自警勿碰。
三國時期,曹操在用人導向上搞了一回生動實踐。公元208年,曹操擔任丞相,分別委任崔琰、毛玠為丞相西曹掾、東曹掾。兩人一起負責官員選拔、任免,“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品行不佳)者,終莫得進”。他們選拔敦厚務實的人才,排斥隻會空談的浮華之人﹔任用謙虛和睦的長者,壓抑結黨營私的小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結果就是“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曹操知道后,嘆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這就是用人導向的力量。當然,古人運用起來過於粗疏簡陋,屬於“初級版”,以致出現了一些“副作用”。后來即如丞相掾屬和洽所言:“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這就是過於機械的標准帶來的負效應,導致人們隻通過外表來判斷清廉與否,更導致官員故意投人們所好裝可憐。所以,和洽對曹操說:“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意思是,那些過於詭誕的行為,往往會包藏虛偽﹔那些有悖常理的行為,往往會衍生奸邪。這恰恰說明,樹立用人導向也必須精准,結合實際,因勢利導,而不可偏執一端。
梳理古代雄主的用人謀略可以發現,在德上的考量,大體合乎前述魏征的判定。特別是在承平之世,對德的如此強調尤令今人深思。很多時候,一些不良細行看似微不足道、無傷大雅,甚至讓許多人內心裡認為大可不必如此較真,但若真放任這些道德上的污點,則必如“蟻穴”,產生“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的惡性效應,久而久之可潰千裡之堤。相反,強調“非才行兼備不可用”,把德的要求放在優先位置,就在無形中樹立了強有力的導向,如唐太宗言,產生“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的良性效果。
時代不同,條件有異,用人的方略也必然有變。師古而不泥古,取其精華而鑒今,對今天的治道方能有所裨益。(陳家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