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讀書論世:人機相較,價值觀是優勢
 |
|
|
日本朝日電視台2016年5月報道,一篇人工智能所創作的小說,由公立函館未來大學團隊提交,竟在1450篇參賽作品中瞞天過海,闖過“星新一獎”的比賽初審,讓讀者們大跌眼鏡。說這篇小說是純機器作品當然並不全對。有關程序是人設計的﹔數據庫裡的細節、情節、台詞、角色、環境描寫等各種“零部件”,也是由人預先輸入儲備的。機器要做的,不過是根據指令自動完成篩選、組合、推演、語法檢測、隨機潤色等類事務。不過,這次以機勝人,亦如前不久棋弈等領域裡的以機勝人,已儼如文學革命的又一個元年。有了這一步,待算法進一步發展,數據庫和樣本量進一步擴大,機器人文藝事業大發展和大繁榮想必指日可待。
到那時,讀者面對電腦,也許隻須往對話框裡輸入訂單:
男1:花樣大叔。女1:野蠻妹。配角:任意。類型:愛情/懸疑。場景:海島/都市。主情調:憂傷。宗教禁忌:無。主情節:愛犬/白血病/隕石撞地球。語調:任意……
諸如此類。隨后立等可取,得到一篇甚至多篇有板有眼甚至有聲有色的故事。其作者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機器,也可能是配比不同的人(HI)機(AI)組合——其中低俗版的組合,如某網站上15元一個的“寫作軟件”,差不多就是最廉價的抄襲助手,已成為時下某些網絡作家的另一半甚至另一大半。某個公眾熟悉的大文豪,一個多次獲獎的馬先生或海倫女士,多次發表過感言和捐贈過善款的家伙,在多年后被一舉揭露為非人類,不過是一堆芯片、硬盤以及網線,一種病毒式的電子幽靈,也不是沒有可能。
法國人羅蘭·巴特1968年發表過著名的《作者之死》,似已暗示過今日的變局。但作者最后將死到哪一步,將死成什麼樣子?是今后的屈原、杜甫、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曹雪芹、卡夫卡都將在硅谷或中關村那些地方高產爆棚,讓人們應接不暇消受不了以至望而生厭?還是文科從業群體在理科霸權下日益潰散,連萌芽級的屈原、杜甫、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曹雪芹、卡夫卡也統統夭折,早被機器人逼瘋和困死?
技術主義者揣測的也許就是那樣。
有意思的是,技術萬能的烏托邦卻從未實現過。這事需要說說。一位美籍華裔的人工智能專家告訴我,至少在眼下看來,人機關系仍是一種主從關系,其基本格局並未改變。特別是一旦涉及價值觀,機器人其實一直力不從心。據說汽車自動駕駛系統就是一個例子。這種系統眼下看似接近成熟,但應付中低速還行,一旦放到高速的情況下,便仍有不少研發的難點甚至死穴——比如事故減損機制。這話的意思是:一旦事故難以避免,兩害相權取其輕,系統是優先保護車外的人,還是車內的人(特別是車主自己)?進一步設想,是優先一個猛漢還是一個盲童?是優先一個美女還是一個丑鬼?是優先一個警察還是三個罪犯?是優先自行車上笑的還是寶馬車裡哭的?……這些Yes或No肯定要讓機器人懵圈。所謂業內遵奉的“阿西莫夫法則”,只是管住機器人永不傷害人這一條,實屬過於籠統和低級,已大大的不夠用了。
美國電影《我是機器人》(2004年)也觸及過這一困境(如影片中的空難救援),堪稱業內同仁的一大思想亮點。只是很可惜,后來的影評人幾乎都加以集體性無視——他們更願意把科幻片理解為《三俠五義》的高科技版,更願意把想象力投向打打殺殺的激光狼牙棒和星際楚漢爭。
其實,在這一類困境裡,即便把識別、權衡的難度降低幾個等級,變成愛犬與愛車之間的小取舍,也會撞上人機之間的深刻矛盾。原因是,價值觀總是因人而異的。價值最大化的衡量尺度,總是因人的情感、性格、文化、閱歷、知識、時代風尚而異,於是成了各不相同又過於深廣的神經信號分布網絡,是機器人最容易懵圈的巨大變量。舍己為人的義士,舍命要錢的財奴……這個世界什麼人都有,每個人又都形跡多端,很難有一定之規,很難納入機器人的程序邏輯。計算機鼻祖高德納因此不得不感嘆:“人工智能已經在幾乎所有需要思考的領域超過了人類,但是在那些人類和其他動物不假思索就能完成的事情上,還差得很遠。”同樣是領袖級的專家凱文·凱利還認為,人類需要不斷給機器人這些“人類的孩子”“灌輸價值觀”,這就相當於給高德納補上了一條:人類最后的特點和優勢,其實就是價值觀。
價值觀?聽上去是否有點……那個?
沒錯,就是價值觀。就是這個價、值、觀劃分了簡單事務與復雜事務、機器行為與社會行為、低階智能與高階智能,讓最新版本的人類定義得以彰顯。請人類學家們記住這一點。很可能的事實是:人類智能不過是文明的成果,源於社會與歷史的心智積澱,而文學正是這種智能優勢所在的一部分。文學之所以區別於一般娛樂(比如下棋和玩魔方),就在於文學長於傳導價值觀。好作家之所以區別於一般“文匠”,就在於前者總是能突破常規俗見,創造性地發現真善美,守護人間的情與義。技術主義者看來恰恰是在這裡力有不逮。他們一直夢想著要把感情、性格、倫理、文化以及其他人類表現都實現數據化,收編為形式邏輯,從而讓機器的生物性與人格性更強,以便創造力大增,最終全面超越人類。但他們忘了人類智能千萬年來早已演變得非同尋常——其中一部分頗有幾分古怪,倒像是“缺點”。比如人必有健忘,但電腦沒法健忘﹔人經常糊涂,但電腦沒法糊涂﹔人可以不講理,但電腦沒法不講理——即不能非邏輯、非程式、非確定性地工作。這樣一來,即便機器人有了遺傳算法(GA)、人工神經網絡(ANN)等仿生大招,即便進一步的仿生探索也不會一無所獲,人的契悟、直覺、意會、靈感、下意識、跳躍性思維……包括同步利用“錯誤”和兼容“悖謬”的能力,把各種矛盾信息不由分說一鍋煮的能力,有時候竟讓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溫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幾乎接近無厘頭),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還是隻能讓機器人懵圈。
在生活中,一段話到底是不是“高級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裝聖母”﹔一種高聲大氣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種節衣縮食是否透出了高貴﹔同是一種忍讓自寬,到底是阿Q的“精神勝利”還是庄子的等物齊觀﹔同是一種筆下的糊涂亂抹,到底是藝術先鋒的創造還是畫鬼容易畫人難的胡來……這些問題也許連某個少年都難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這種人類與生俱來的心領神會,顯示出人類在處理價值觀方面的能力超強而且特異。其實不過是依托全身心互聯與同步的神經響應,依托人類經驗的隱秘蘊積,選擇了一個幾無來由和依據的正確,有時甚至是看似並不靠譜的正確——這樣做很平常,就像對付一個趔趄或一個噴嚏那樣再自然不過,屬於瞬間事件。但機器人呢,光是辨識一個“高級黑”的正話反聽,就可能要癱瘓全部數據庫——鐵板釘釘的好話怎麼就不是好話了?憑什麼A就不是A了?憑什麼各種定名、定義、定規所依存的巨大數據資源和超高計算速度,到這時候就不如人的一閃念?甚至不如一個猩猩的腦子好使?
從另一角度說,人類曾經在很多方面比不過其他動物(比如嗅覺和聽覺),將來在很多方面也肯定比不過機器(比如記憶和計算),這實在沒什麼大不了的。但人類智能之所長往往在定規和常理之外,在陳詞濫調和眾口一詞之外。面對生活的千差萬別和千變萬化,文學最擅長表現名無常名、道無常道、因是因非、相克相生的百態萬象,最擅長心有靈犀一點通。人類經驗與想象的不斷新變,價值觀的心理潮涌,倒不一定表現為文學中的直白說教——那樣做也太笨了——而是更多分泌和閃爍於新的口吻、新的修辭、新的氛圍、新的意境、新的故事和結構。其字裡行間的微妙處和驚險處,“非關書也,非關理也”(嚴羽語),常凝聚著人類處理一個問題時瞬間處理全部問題的暗中靈動,即高德納所稱“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之奇能,多是“萬象俱開,口忽然吟,手忽然書”(譚元春語),“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湯顯祖語),“羚羊挂角,無跡可求”(嚴羽語),“此處無聲勝有聲”(白居易語),其復雜性非任何一套代碼和邏輯可以窮盡。
如果事情就是這樣,我們就隻能想象,機器人寫作既可能又不可能。
說不可能,是因為它作為一種高效的仿造手段,一種基於數據庫和樣本量的寄生性繁殖,機器人相對於文學的前沿探索而言,總是有慢一步的性質,低一檔的性質,“二梯隊”裡跟蹤者和復制者的性質。
制圖:張芳曼
《 人民日報 》( 2017年02月28日 24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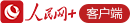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