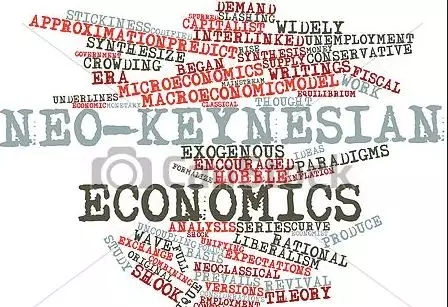
自從凱恩斯主義誕生以來,現代經濟體系一般都意味著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混合。
從處理信息的角度來看,指令性計劃實際上是一種集中式的決策機制,市場則是一種分散化的決策機制。“市場決策是由參加市場活動的許許多多個企業和個人根據各自的利益而做出的,決策的分散性是市場決策的固有特征”。
到今天,恐怕已經很少有人會認同完全的計劃和集中,或是徹底的自由和放任。問題在於,什麼時候需要集中力量,什麼時候需要分散決策?(本文的“分散決策”是指市場多元主體自發做出經營決策的行為,不涉及黨政內部)
這就涉及到一個根本性問題:集中與分散、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究竟在哪裡?經濟學對此有很多解答,其中最清晰也是最具有操作性的一條標准,應該是信息的完備程度。
集中或分散
早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就發現,國際組織總是給很多后發國家推銷“華盛頓共識”目錄下的政策,結果給這些國家帶來災難。顯然,我們不能陰謀論,認為國際組織就是要讓其他國家生亂。但問題在於,為什麼自由主義政策在發達國家(先發國家)比較適用,而在發展中國家(后發國家)常常會失靈呢?
這是因為,先發國家與后發國家的信息完備程度完全不同。對先發國家來說,邁入現代文明是一個“從0到1”、從無到有的創造過程,沒有足跡可循,面臨著巨大的未知和不確定性,這時候,就需要通過市場機制,實現決策和信息處理的分散化,讓不同的群體、企業甚至國家能夠進行多樣的探索。
但是對后發國家來說,上述的不確定性大大降低,甚至是不存在了,很多發展目標不需要再“從0到1”進行創造,而是“從1到N”的擴散過程,隻需要模仿和學習先發國家,這時候,利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往往能夠更有效率地實現趕超。
正因此,后發國家往往比先發國家更需要發揮政府的力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早就指出,“政府在后發國家的作用更大”。科學界流傳一句名言:原子彈最大的秘密是知道它可以制造出來。這是因為,一旦知道原子彈可以制造出來,那麼關於原子彈能否造出來的不確定性就不存在了,隻需要政府集中科研力量進行集中攻關就好了。
但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探索未知、面臨較大不確定性時,集中力量攻關就有可能會陷入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的困境,這時候分散決策、多元嘗試和不斷試錯,就是至關重要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如果集中力量貿然選擇一個方向,風險將很大。
由此,究竟什麼時候應該集中或分散,取決於目標的不確定性程度。如果目標是確定的,信息是完備的,就應該更多採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法。反之則應該更多採取分散決策和多元嘗試的方法,給予市場主體和企業家群體自由發揮的空間。
可見,集中和分散都有適用的范圍,但都不能包打天下,正因此,它們不應該相互排斥,而應該形成互補。對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為了達到某具體的目標,這類經濟優越於無計劃的經濟,因為無計劃的經濟沒有具體的目標。計劃經濟在形成戰爭力量方面是比較優越的,這就是戰時各類經濟所以全都納入高度計劃的原因。在施行高水平的資本形成時、在創建某一大產業部門或計劃制訂者給自己規定任何其他的單一目標時——如灌溉沙漠、建筑房屋或其他,計劃經濟也是比較優越的。如果沒有必須集中努力去實現的單一目標,計劃經濟便不如無計劃經濟。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個人做出的判斷同在中央的計劃制訂者的判斷會是一樣的或優於后者﹔因為不存在經濟應向哪裡發展的單一方向﹔因此,最好讓每個人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去自由地充分利用他所能得到的資源。無論企業家是私人還是政府官員,這一點都同樣適用。

“集中力量辦大事”
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到它自身就融合著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就像一個巨大的容器,裡面裝著先后不同的時間。在中國,既有需要趕超和模仿的目標,也有需要創造和引領的目標。
這就決定了,中國改革將綜合運用集中和分散、政府和市場兩種力量,用集中攻關來實現后發領域的追趕,用分散來實現前沿領域的超越,這樣就能既以最快的速度實現模仿和追趕,又以多元的嘗試應對未知和不確定性。
中國的經濟改革引入了市場機制,但中國從來沒有放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原則,在改革的過程中仍然注重發揮這一制度優勢。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這樣一個共識: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代,與改革開放后的市場經濟時代,有一個線索是一以貫之的,這就是同樣注重從國家層面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中國在航天領域的突飛猛進,正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這些年來,“從東方紅一號衛星,到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從長征系列火箭的首飛,到即將迎來的長征五號大型火箭發射﹔從航天英雄楊利偉一飛沖天,到景海鵬三次進入太空,中國載人航天進入第二十五個年頭,六次載人飛行把11名航天員送入太空,逗留太空的時間也從一天延長到三十天” 。外媒評價說,中國航天業“突破力”令世界羨慕。
這個突破力,就來自於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因為這個領域,技術的成長階段發達國家已經經歷過,因此中國隻需要在此基礎上攻關就好。
同時,在高鐵和大飛機領域,中國都取得了快速的進步。尤其是高鐵,隨著“復興號”跑出350公裡的時速,中國高鐵已經實現了幾乎完全的自我研發和自我設計。
而以上所舉例子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有發達國家在這些領域的先發經驗可以模仿,目標非常明確,因此集中力量進行趕超的效率就非常高,並且可以在此基礎上,最后實現彎道超車。

創新演化
哈耶克有一段精彩的論述和比喻:“人類在改善社會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就必須明白,他不可能獲得主宰事務進程的充分知識。因此他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樣去模鑄產品,而是必須像園丁看護花草那樣,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識,養護花草生長的過程。”
這個比喻非常精彩,器皿是一個沒有生命力的器物,它是通過設計出來的,因為人類掌握了制造器皿的全部知識﹔但花草卻是有生命力的有機體,它的生長過程難以設計,因此,最好的方法是為花草的生長提供良好的環境,讓花草能夠自由生長、釋放內在於自身的可能性。
這就像市場主體進行創新一樣,沒有人能夠預先知道市場主體會創造出什麼樣的新產品,也不可能預先制定誰最終勝出。因此,政府應該做的,就是為各種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良好的發展環境,恰如園丁看護花草那樣。中國改革走過40年進程,從政府到社會已經逐步形成這樣的共識:偉大的企業和偉大的產品,都不是政府官員能夠坐在辦公室裡預先計劃出來的,而必須依靠市場主體的自發探索和多元嘗試。
事實上,隨著中國市場體系日益發育成熟,這種超出人預料的創新能力也逐步展示出來。中國的移動電子支付滲透到各個領域,從五星級的高檔酒店,到街邊賣水果的小攤販。這甚至讓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感嘆,“我的部長在上海買栗子像個鄉巴佬”。中國的共享單車也開始進入歐美市場,數字經濟也處在領跑狀態,尤其在人工智能這一前沿領域,與美國形成分庭抗禮之勢。
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中國越來越善於培育市場環境,激發企業家群體的創新活力。習近平曾說:“激發市場活力,就是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該營造的環境營造好,該制定的規則制定好,讓企業家有用武之地。”
在市場經濟中,經濟活動的決策權分散給個別的企業和個人,而每個企業家的目標、偏好、預期也各異,因此,這就形成了多元的探索和嘗試,就能夠開拓更多可能性。
中國在前沿領域的創新能力充分說明,市場機制帶來的分散決策、多元嘗試和激烈競爭,更能有效應對未知和不確定性,能夠指向未知的目標,創造出全新的事物,為社會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第三條道路”
英國思想家卡爾·波蘭尼從一種獨特的視角來認識市場經濟,他認為,市場實際上是“嵌入”社會之中的,“管制和市場是同時生長的”。偉大的思想家、經濟學家科斯則這樣形容企業:“在不自覺的統籌協調的大海中的自覺力量的小島,它們如同凝結在一桶黃油牛奶中的一塊塊黃油”。市場的大海無法淹沒企業的小島,而企業的小島更不可能完全佔據大海,就這樣,市場這個自發的力量與企業這個計劃的力量,就形成了一種共存共榮的混合形態。
集中與分散,計劃與自由,都有其合理性,一個理想的制度不是在二者中走極端,而應該按照適當的方法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從而把兩種力量都運用起來。中國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要求共同發揮政府和市場、集中和分散、計劃和自由這兩種力量,並且走出了一條成功的中間道路或者說“第三條道路”。
尤其是當前,在一些領域,中國仍然處於后發趕超的階段,仍然需要集中力量進行攻關﹔但在另一些領域,中國已經走上世界前列,甚至進入創新的“無人區”,面對著巨大的不確定性,隻能依靠自主創新走出一條新路,這又需要通過市場機制激發人們的多元探索。
幾個世紀以前,偉大的思想家托克維爾作出了一個驚人的預言: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人以個人利益為動力,任憑個人去發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為此目的,俄國人差不多把社會的一切權力都集中於一人之手……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宰世界一半的命運。
托克維爾沒有想到,在世界的東方,當中國人進入現代化浪潮中,他們從古老的傳統文化裡繼承了一種包容性的思維方式。中國人不是用排他性的眼光而是用一種包容性的眼光看待這二者,並致力於將政府與市場納入到一個框架之內。
美國和蘇聯都曾一度“各主宰世界一半的命運”,但中國改革體現的“包容型智慧”和中間道路,則預示著人類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文/李拯
文章整理自《中國的改革哲學》,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