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勿忘更多坐冷板凳的“陈忠实”
对民族文化的积累、保存与贡献而言,很多情况下,成就与光环是不成正比的——镁光灯不停闪烁的地方,未必是文化高地;而远离光耀的僻静之处,却屹立着文化高峰。
近期,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逝世引来如潮纪念,这位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代表,配得上各种礼赞。在《白鹿原》的题记里,陈忠实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道出他的文学追求,而他也确实用作品努力攀爬这样的高度。有人形容陈忠实的离世堪比“中国文坛的天空塌了一个角”,此言并不夸张。
只是此时此刻,笔者却不能不想起另一个“史学界的陈忠实”。他的名气远没有陈忠实大,但是他的离去同样令人扼腕,他的成就同样足以载入史册,他就是前不久英年早逝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刘浦江。
这位1961年生于上海的年轻学者,仅仅活了54岁,在淋巴癌晚期的时刻,他用最后的生命冲刺,带领团队完成了《辽史》的修订。这整整一百一十六卷的《辽史》,跟《白鹿原》的“文学丰碑”一样,成为一座“史学丰碑”。
支撑这两座丰碑的,是背后令人赞叹不已的那种“坐冷板凳的功夫”。陈忠实写《白鹿原》,从构思到写成,差不多用了近十年时间,其中很长一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农村的陋室里,远离尘嚣,全情投入。写完后的某一天,他忐忑不安地等待评论家李星的评点,得到的是一声惊呼:“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正是这句关中民间最常用的口头语,给陈忠实铸下了永久的记忆。他明白,所有的艰辛有了回报。而后来的回报如此丰厚,他自己也始料未及。陈忠实的“冷板凳”,给他带来了热腾腾的文学春天。
相比之下,刘浦江教授的“冷板凳”,或将是永无止境的。即便“弄成”了卷帙浩繁的皇皇《辽史》,也只算在相关领域“弄出点声音”,无论大众还是媒体,对于它的价值认定,难免存在隔膜和生疏。辽宋夏金元属于多民族竞争时期,这些政权分别由不同的民族所建立。史学界对于辽史的研究,不说是偏门,也至少是冷门,有学者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全部“二十四史”点校本,印数最少的就是《辽史》,可见《辽史》和辽史研究的寂寞。
但再寂寞,也得有人做这件事,相伴而来的,就是长期的“坐冷板凳”。对很多学者而言,这就是一个“终身姿势”,无论你“弄成”什么,可能安慰你的,只是一份“完成心愿”的踏实,而见不到烁烁闪耀的光环。但是对民族文化的积累、保存与贡献而言,很多情况下,成就与光环是不成正比的——镁光灯不停闪烁的地方,未必是文化高地;而远离光耀的僻静之处,却屹立着文化高峰。
我们不要忽视和忘却蛰伏在僻静处的“坐冷板凳者”。他们足够伟岸,但也足够寂寞。文学界的陈忠实轰轰烈烈地走了,史学界的刘浦江冷冷清清地走了。冷清没有关系,甘坐冷板凳的刘浦江教授不会计较身后的哀荣。但是作为我们,面对两种“坐冷板凳”的身形,不妨稍稍“分神”,将目光聚焦一下刘浦江和他的《辽史》,陈忠实勾勒了一个民族的“秘史”,而刘浦江们描绘了一个民族的“正史”,他们都值得人们永久祭奠和纪念。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相关新闻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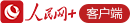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