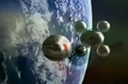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表明,我们党对宪法权威在法治建设中重要地位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宪法是人类文明的产物,缘起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宪法和资本主义宪法的分野。从历史上看,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和法治体系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存在根本区别。
(一)
《决定》指出,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指导。
任何形态的法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法学基础理论之上的,而不同的法治与宪政,其理论渊源与思想基础存在本质区别。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宪政立足于“社会契约”和抽象正义、理性等自然法学思想,在反对君权神授、实现形式法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证明。无论资本主义宪政发展出多么精巧的违宪审查和司法机制,并致力于实现从理念到制度再到应用技术的转变,但由于其价值理念不符合中国国情,因而不可能用于指导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
任何法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都决定于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宪政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要求,而社会主义法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宣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始终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规律。从初级阶段“先粗后精”的立法模式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从法律意识到法治精神、法治文化,再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我国法治建设致力于解决现实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而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人民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本质属性,凸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与理想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的客观必然,从而使法治建立在深厚的现实基础之上。
(二)
从表面上看,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宪政似乎超越于政党制度,其实不然。无论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或其他形式,资产阶级政党从来没有超然于法治之外,都极力通过竞选、大选谋取议席来控制法治机关和法治运作,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法治中国建设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会决定围绕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提出“三统一”“四善于”,并作出了系统部署。所谓“三统一”,是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对这一点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所谓“四善于”,就是“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这一重要论断,一是符合宪法、法律。我国宪法庄严宣告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就从根本大法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二是符合规律。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以确立和巩固的,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必然,把党的领导全方位贯彻到法治各个领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一点也得到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的确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三是符合法律价值。法治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正义,终极追求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权利。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
党与法治体系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领导关系。即党对立法具有领导权,具体包括三种权力:立法决定权,指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性立法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修宪提议权,即宪法修改建议应由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听取报告权,即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问题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当然,这并不是以党代法,而是旨在规范党法关系,确保法的价值优良性。二是保证关系。即党保证严格执法,为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提供后盾和保障。既反对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又要通过党依法执政能力的提高和全体党员法治思维、法治能力的提升,为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创造条件。三是支持关系。即党支持公正司法,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一方面,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另一方面,始终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级司法机关党组的作用。通过司法机关人财物由省级统管及跨行政区域司法机关的设置等体制机制改革,排除外界对司法不当干预,确保司法公正。四是服从关系。即指党带头守法,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结合起来,坚持依法执政,树立法治信仰,弘扬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三)
国家权力的分配、运行和监督机制,是法治的核心议题。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分权思想即已萌芽。英国资产阶级理论家洛克提出了行政权、立法权分立的思想,法国的孟德斯鸠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分立即所谓的“三权分立”论。通过宪法实现权力分立和制衡被视为资本主义宪政的“奥秘”。社会主义法治始终坚持一分为二地对待法治历史遗产。邓小平同志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习近平同志强调制度性反腐的重要性,指出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这里的权力监督制约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下“三权分立”存在本质不同,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始终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支撑法治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权力渊源上,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强调主权在民,以抽象的社会契约论为渊源。实际上,在代议制民主下,其权力代表性明显存在缺陷。以英国为例,其上议院议员是世袭制,且根深蒂固,难以改变。我国宪法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决定》强调民主立法,拓宽公民有序参与途径,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工作专家制度,以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充分体现人民意志。
在权力结构上,不同于西方三权鼎立的权力配置,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渊源于此。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可见,这是一种不同于横向平行模式的纵向权力结构模式,有利于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在权力监督上,世界上没有定于一尊的模式。实际上,即使在西方,权力制约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难以统一,主要有英国的议会至上、美国的三权制衡、法国兼采议会制和总统制的混合体制等。我国的法律监督体系由国家监督、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三大部分构成,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运行。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决定》指出,对行政权的监督体系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构成;对司法权的监督体系包括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监督、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以及人民群众、政党、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的监督。这种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最大不同在于:一方面,不是通过在朝党和在野党相互抗衡,而是在民主协商、多党合作的前提下进行相互监督;另一方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负责宪法实施,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确保行政权和司法权得到正确行使。
(四)
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是以“人权”对抗神权而获得所谓“合法性”的。社会主义法治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奉行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在人权保障上,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有独特之处。
人权主体不同。西方人权观念认为人权的主体仅仅是个人,从而使个人和社会分离开来,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似乎成了不可共存的两种人权观。我国人权保障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为基础,从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原理出发,明确提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体现了民族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的高度统一,并最终通过让所有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而将人权落实于现实的个人主体。
人权客体不同。人对自身的支配关系和人对政治联合体的支配关系,是西方人权观所关注的对象。然而,人不仅是生物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动物,要过自然与政治生活,而且是经济动物、文化动物,还要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中塑造“生态人”的属性。因此,社会主义法治既要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和政治利益,又要保护公民的经济利益以及社会文化权益。为此,我国依法治国方略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发展战略水乳交融、有机统一,为全方位地保障人权奠定了基础。
人权保障重心不同。我国不仅强调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性,而且更加重视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早在2001年就已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改变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谋求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公平发展,我国将生存权和发展权定位为两项基本人权。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发展权在全球显得更为紧迫与必要。这已经从一个概念变成为国家人权战略和人权实践。
人权救济方式不同。西方过分强调对抗与对立,我国则将积极保障与消极保障、立法护权与司法救济相统一。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群众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公民陪审以及司法审判的执行各方面落实人民司法这一基本方针。通过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全面实现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实体性权利,实现公正审判权、人道待遇权、回归社会权等程序性权利,实现司法救助权、法律援助权和律师帮助权等综合性权利,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以司法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以社会正义促进司法正义。
(作者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4年11月06日 07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